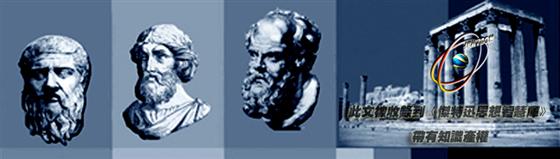
《物种起源》--[第二章]解读
第二章 自然状况下的变异
从第二章起达氏将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继续讨论物种的遗传与变异的规律,在讨论中达氏还会经常与家养物种的遗传和变异二者之间做对比分析,我们在总结这章中达氏的观点还是利用现代生物学研究成果和结论对比分析,最终能够使我们对自然环境条件下物种的遗传与变异的规律有所深刻的认识。
关于变异性课题的分析,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变异性”(variability),所谓变异性是指生物体内发生变化的属性和能力。生物体遗传性可以改变的一种特性。在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当环境条件不符合其遗传性的需要时,这种生物体或者死亡,或者被迫同化这种新的条件,通过新陈代谢类型的改变,形成与其亲代不同的性状,即遗传性发生了变异。这些解释是现代生物理论研究的成果,但是在150年之前,人们对“变异性”还不能拿出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正如达氏所讲的“我也不在这里讨论加于物种这个名词之上的各种不同的定义。没有一项定义能使一切博物学者都满意;然而各个博物学者当谈到物种的时候,都能够模糊地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这名词一般含有所谓特殊创造作用这一未知因素。”
但是,当时的人们认识到物种畸形这个概念,达氏“认为畸形是指构造上某种显著偏差而言,对于物种一般是有害的,或者是无用的。”这种认识与现代生物学认识是基本相近的。
对于变异这个词汇,用我们今天的解释就是“同一起源的个体间的性状差异。主要指子代与亲代在外形、内质上的差异。在一种生物类群中,亲代和子代之间,子代的个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是遗传的相对。变异特性可以导致生物进化,促进生物新物种出现。”可是在过去那个年代还没有完全解释十分清晰,我们来看达氏的解释,“变异”这一名词的,它的含义是直接由物理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一种变化;这种意义的“变异”被假定为不能遗传的;我认为在这种情形下,这些类型是可以称为变种的。从达氏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达氏将“变异”解释成为“变种”,并且出现了一种矛盾,假定变异不能遗传,那么出现的变种是否说明就是一种另类物种,这与我们今天生物理论好像有一些相桲。
关于这种畸形变异是否能够在自然状况下能否永久传下去,达氏采取的是值得怀疑的态度。达氏认为“几乎每一生物的每一器官和它的复杂生活条件都有如此美妙的关联,以致似乎很难相信,任何器官会突然地、完善地产生出来,就像人们完善地发明一具复杂的机器那样。”达氏还认为即使这种畸形变异能够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出现,那么也会逐渐消失掉的,他讲到“如果这种畸形类型确曾在自然状况中出现过,并且能够繁殖(事实不永远如此),那未,由于它们的发生是稀少的和单独的,所以必须依靠异常有利的条件才能把它们保存下来。同时,这些畸形在第一代和以后的若干代中将与普通类型相杂交,这样,它们的畸形性状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失掉。”
在个体差异课题讨论中,达氏能够将这个概念解释的比较清楚,他的解释是“在同一父母的后代中所出现的许多微小差异,或者在同一局限区域内栖息的同种诸个体中所观察到的、而且可以设想也是在同一父母的后代中所发生的许多微小差异,都可叫做个体差异。”同时对个体差异还能有进一步的认识,达氏阐明“个体差异它们常常是能够遗传的;并且这等变异为自然选择提供了材料,供它作用和积累,就像人类在家养生物里朝着一定方向积累个体差异那样。个体差异不经能够在不同生物体中产生,按照达氏的观点”个体差异有时在同种诸个体中也会发生变异。我们再利用现代生物学理论对比分析,现代生物学认为“个体差异”是指基本情况相同时,大多数物种变异过程是相近的,但也有少数物种会出现与多数物种在性质和数量上有显著的差异,产生个体差异的原因是广泛而复杂的。现代观点与达氏观点同样是接近的。
在讨论个体差异时候,达氏还注意研究了同个体差异相关连的“变形的”(protean)或“多形的”(polymorphic)那些属,他发现在这些属里物种表现了异常大的变异量。在大多数多形的属里,有些物种具有稳定的和一定的性状。除了少数例外,在一处地方为多形的属,似乎在别处也是多形的。达氏表示出对此感到十分的困惑不解。
对于属的认识今天我们有两种解释,其一,属表示物种的种类;其二,属代表生物学生物分类法的一个级别,在科以下,种以上。例如鱼类分类表的划分,动物界——脊索动物门——鱼类——总纲——纲——亚纲——总目——目——科——属——种。达氏在这里主要从属表示物种的种类变异量很大方面出现困惑的。
关于可疑的物种的分析达氏只这样认识的“有些类型,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物种的性状,但同其他类型如此密切相似,或者由中间级进如此紧密地同其他类型连接在一起,这些可疑的和极其相似的类型有许多曾在长久期间内持续地保存它们的性状,它们和良好的真种一样长久地保持了它们的性状。”还有就是在讨论可疑物种过程中达氏对个体差异形成过程划分了阶段,并将个体差异看作是程度变异的初步阶段,他讲到“我认为个体差异是走向轻度变种的最初步骤,在任何程度上较为显著的和较为永久的变种是走向更显著的和更永久的变种的步骤;并认为变种是走向亚种,然后走向物种的步骤。接着他又讨论了导致个体差异变化的因素,他指出”从一阶段的差异到另一阶段的差异,是由于生物的本性和生物长久居于不同物理条件之下的简单结果;关于更重要的和更能适应的性状,从一阶段的差异到另一阶段的差异,可以稳妥地归因于自然选择的累积作用,以及器官的增强使用和不使用的效果。”
按照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成果解释,物种形成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较常见的方式是经过长期的地理隔离而达到生殖隔离,生殖隔离一经形成,原先的一个物种就演化成的两个不同的物种。这种演化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
不同物种间都存在生殖隔离,物种的形成必须经过生殖隔离时期,但不一定要经过地理隔离,如在同一自然区域 A物种进化为B物种。但是在地理隔离基础上,经选择加速生殖隔离的形成,所以说经地理隔离、生殖隔离形成新物种是物种形成常见的方式。
从上述理论的论述就可以使我们对达氏的这种观点很好地理解了。
关于分布广的、分散大的和普通的物种变异最多的讨论,我们要将其分为两个部分理解,第一部分是分布广的物种变异,这方面的总结是由得康多尔和别人曾阐明的,分布很广的植物一般会出现变种;这是可以意料到的,因为它们暴露在不同的物理条件之下,并且因为它们还须和各类不同的生物进行竞争。第二部分分散大的和普通物种变异观点是达氏总结的,“在任何一个有限制的地区里,最普通的物种,即个体最繁多的物种,以及在它们自己的区域内分散最广的物种(这和分布广的意义不同,和‘普通’亦略有不同),最常发生变种,而这些变种有足够显著的特征,足以使植物学者认为有记载的价值。因此,最繁盛的物种,或者可称为优势的物种,——它们分布最广,在自己区域内分散最大,个体亦最多——最常产生显著的变种,或如我所称的,初期的物种。”
达氏继续阐述另一个观点,就是物种为什么能够长期存活的课题,他认为“这恐怕是可以预料到的一点;因为变种如要在任何程度上变成永久,必定要和这个区域内的其他居住者相斗争;已经得到优势的物种,最适于产生后代,这些后代的变异程度虽轻微,还是遗传了双亲胜于同地生物的那些优点。”这里说明达氏已经将物种能够得到优良的遗传归咎于物种之间的相互斗争。
达氏进一步要说明物种之间相互斗争的优势,他将斗争的优势归结为斗争的类型,这种类型具体体现在“同属的或同纲的具有极其相似生活习性的那些成员而言。”另外这种斗争的类型还体现在物种的“个体的数目,或物种的普通性,其比较当然只指同一类群的成员而言。”这就是说,在每一个纲中是大属的那些普通的、广为分散的、以及分布范围广的物种;而且这些物种有把它们的优越性——现今在本上成为优势种的那种优越性——传给变化了的后代的倾向。
关于各地大属的物种比小属的物种变异更频繁观点的阐述,达氏认为从物种的属上分析物种的种类,大属物种比小属物种更具有优势,他阐述道“如果把记载在任何植物志上的某一地方的植物分作相等的二群,把大属(即含有许多物种的属)的植物放在一边,小属的植物放在另一边,当可看出大属里含有很普通的、极分散的物种或优势物种的数目较多。”那么,我们就要追问,是什么原因产生这种观点的呢?达氏继续解释为“由于我把物种看作只是特性显著而且界限分明的变种,所以我推想各地大属的物种应比小属的物种更常出现变种;因为,在许多密切近似物种(即同属的物种)已经形成的地区,按照一般规律,应有许多变种即初期的物种正在形成。”
关于大属里许多物种,正如变种那样,有很密切的、但不均等的相互关系,并且有受到限制的分布区域。在大属里的物种和大属里的有记载的变种之间,达氏认为有一种关系存在,由于在物种和显著变种的区别方面,人们还不可能建立准确无误的衡量标准,当时人们还不可能完全掌握物种和变种之间的遗传关系,只有依靠物种之间的差异量来作决定,一般来讲物种之间的差异量要大于变种之间的差异量,也就是说变种是正在形成的初步物种,变种的演化归宿就是形成一种新物种。从哲学角度看,变种是量变级生物形态,物种是质变级生物形态。另外达氏又总结出“变种的分布范围一般都受到了很大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