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的论证与辩论分析课,接着讨论论争中的定义策略。但是在这之前,我给同学们的参考书目中添了这样一本——
这是我在五一放假期间通过当当网订购的一本书,线索是前不久在《中国报道》杂志去年第11期“月读”栏目看到的一篇书评《当谈论“扯淡”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编辑推荐”的“推荐理由”写道:“本书用各种逻辑方法,为我们解读了美国五花八门的新闻事件,揭露了政治人物如何用“扯谈”的把戏蒙骗大众”。
当时我本能地感到,这是我的“论证与辩论分析”课用得着的参考书。拿到后一看,果然不错。实际上,它的写作方法与我给同学们推荐的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逻辑学家斯泰宾的《有效思维》差不多,都是对当世政治人物说服性言论进行谬误分析,具有批判性思维的特点。只是这本由两位美国当代自由撰稿人写作的《说服的力量》比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位英国逻辑学家的《有效思维》,在风格上更为俏皮,对谬误的揭露和嘲讽更为辛辣,但其逻辑的分析方法还是一丝不苟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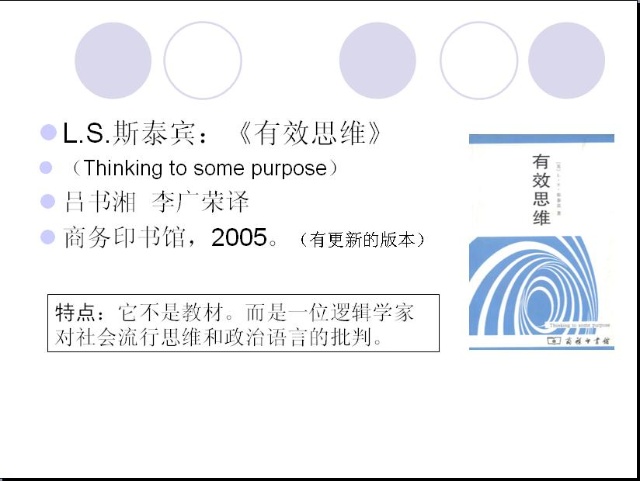
因此,虽然已经讲完了“谬误分析”一讲。但在晚天的课上,我还是忍不住给同学们介绍了这本书对一个“滑坡谬误”的分析。
我之所以介绍这个案例,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我课上以《批判性思维与传播》中的一个案例说明滑坡谬误时,课上有同学觉得那个滑坡谬误仍然对她具有说服力,我自己内心也难以否认它对我的说服力。所以,当我在《说服的力量》中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和那位同学都可以得到某种解脱:
那么,《说服的力量》的两位作者真的认为上面那段参议员的话,不是一个谬误吗?没那么简单。他们进行了如下的分析:
这一层分析,实际上是通过寻找推理前提、判断标准以及不同行为之间的相似性,以确认它们符合同一个标准和前提。这实际上是一个类比思维的过程,其倾向是“证立”而不是“证否”。
再看下面一层:
这一层分析,则与上面的思维过程相反,它着眼于辩识参议员提到的不同性行为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只有“通奸”这种行为与最高法院可能做出的判决的那种性行为具有相似性,而“乱伦”、“重婚”、“多婚”,则因为要牵扯到其他人,即超出了两个人自愿的关系,而不符合“唯一的考虑因素是私人权利”这样一个前提和标准。也就是说,不可能由最高法院判决“你有权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生双方同意的[同性]性行为”合法,而自动产生“乱伦”、“重婚”的结果。
实际上,在我公布这本书的分析结果之前,在讨论中,就已有同学提到这几种行为之间的不同:比如,有一位同学(我记不清是谁了)指出,重婚、多婚这种需要法律确认的行为与两个人之间自然的性行为的性质肯定不同。而尚昊同学则指出:后者涉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超出了两个人之间的性关系。这差不多正是这本书两位作者的着眼点。
而我要给同学们介绍这个案例,其实并不是为曾经介绍过的滑坡谬误补充一个案例,而主要是为了介绍两位作者分析这个谬误的思维过程。
尽管如此,这个分析仍然没有说服课堂上的一位同学。而我记得,本学期第一次课后,正是这位同学针对辩论赛中曾遇到的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向我提问,并坚持“乱伦”(这样直接说出来太吓人了,它可能指的只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可能偶然产生的恋爱_我自己做编辑时就曾收到过这样一对痛苦的情侣的来信)也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必须承认,逻辑的论证和分析,不可能说服所有的人。这可能是因为,你觉得有差异,他觉得没差异——事物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在不同的人们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这里面不完全是事实性因素,还可能有价值性因素。我无法代替《说服的力量》的作者说服我的一位学生,如果他们这样一番分析仍然不能说服他人的话。我们这个课,主要也不是用论证来说服学生,而是向学生们介绍论证和说服是怎样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