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剥下旧制度“吃人”的画皮
文=曹喜蛙 油画=丁秋发
小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对王全安电影的改编基本满意,不是瞎说的。院线版的王全安电影《白鹿原》我看了,尽管依然有些硬伤,但是整体上对原著史诗的故事把握的还是十分到位,其中大刀阔斧的删繁就简还是非常可圈可点。
我以为对小说《白鹿原》的改编可以有无数个版本,原来的舞台剧版本我没有看过,在这里不好说。但是王安全的电影改编如果说有硬伤的话,就是删减的还不够狠,还有些拖拖拉拉,之所以有观众说有点看不明白,就是因为电影很多地方对陈忠实的原著还是很迁就,正因为很迁就,也就难免不总想交代但总也交代不清,开头的部分也就显得寥寥草草,一方面想交代清楚,所以总也不想、总也舍不得删减,另一方面却总也演绎扩展不开,给观众一头雾水的感觉。
我理解的改编,其实也就是以小说的原著中的素材和人物,进行二次创作,类似翻译中的“意译”,而不是简单的“直译”。电影改编的好的地方就是使用了“意译”的方法,不好的地方就是生硬的“直译”。尤其,用电影的画面艺术去翻译小说的语言艺术是十分的难的,很多时候作家的几句话就能让人无限遐想,而电影堆砌的一堆画面则常常让人不知道在说什么。
电影以1938年结尾其实是相当有深意的,也符合当下的国情,至于原来小说中更深层次的阐释其实在现有的故事情节中也给予关照。事实上,不管在小说还是在电影里,都注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进行鞭挞,比如小娥死后,黑娃带土匪到白嘉轩家那一场戏,就把很多内容压缩在一起,把小说中的几场戏压缩到一起了。小说里是几次土匪洗劫,电影里只能一场戏,本来是土匪把白嘉轩的腰板砸坏了,电影里是黑娃直接砸坏的,而且加上不错的对话“反正都是害人”。

丁秋发 油画 给椅子洗个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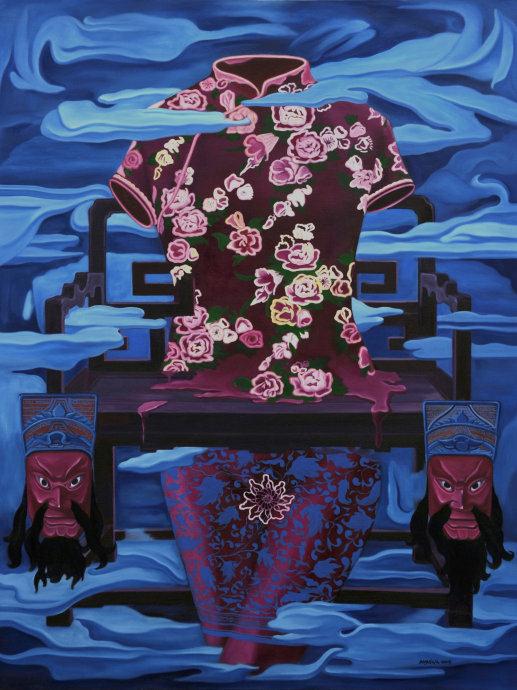
丁秋发 油画 旗袍
小说里,小娥没有怀过孕,而电影里小娥却为白孝文怀上了孩子;小说里,白孝文是没有被抓壮丁的,而在电影里白孝文被抓了壮丁,而且听一个壮丁油子讲以后的天下是共产党的,暗示了白孝文将来加入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尤其,白孝文是知道小娥为他怀上孩子后卖身当兵救小娥和孩子的。而恰恰鹿三杀死小娥的那场戏,改的也非常好,一个是小娥对进来的鹿三说她饿了,类似小说中白孝文的媳妇对白嘉轩说的那段话,而小娥对鹿三说她对不起黑娃则实际上与代表封建思想白嘉轩和被封建思想洗脑了的鹿三、小娥等走到一个时代的悲剧的重点。
电影里黑娃与小娥的相互吸引和爱恋要相对直接,比小说要更加简洁,适合当代的电影观众理解。尤其黑娃与麦客打架等情节都很不错。电影的画面语言提炼的“秦腔”“麦浪”,尤其增加的黑娃与小娥在麦垛上的野合,都非常有诗意,是纯粹的电影语言,发挥了电影的长处。电影里的瘟疫季节,一帮村民要求给小娥修庙塑像,而白嘉轩强调修塔镇压,而且为了彻底镇鬼,都不惜牺牲自己小娥肚子里白嘉轩亲孙子的血脉,封建制度吃人的“狠劲”终于暴露无遗,彻底给剥离出了那张伪善、害人的“画皮”。
需要指出的是电影虽然号称经过很多年的打磨,但是对民居的装饰、家居等还是不很考究,比如电影里一再出现的椅子就不是十分讲究,其实是可以请教古典家具专家,能够更精确一些,不能不说电影还是有些美中不足。这也是小说原著不足和硬伤的一个延伸,也是小说《白鹿原》不能与《红楼梦》那样的古典小说名著相提并论的一个因素。
整体上讲,《白鹿原》小说与电影都是瑕不掩瑜,都堪称时代史诗,尤其电影里从田小娥、白孝文、黑娃、鹿兆鹏等弱者、反抗者、革命者,到郭举人、白嘉轩、鹿子霖、鹿三等旧时代的遗老、旧势利的代表、殉道者、牺牲品,彻底剥下了“封建制度”“腐朽思想”吃人的画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