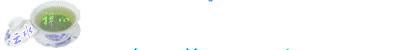|
书缘今生曾梦断
 文 / 林森
|
 |
| 我最早拥有的书,是一堆大大小小的连环画。不记得是怎样买来的,印象中浮起的,只是在窑前墙壁上有一个小而又浅的洞,里面大小错落排放的,是我自己参差不齐的书。书皆卷边,大多无皮无尾,但却是我的宝贝。我常常端一个小凳,半个身子钻进洞里,一翻弄就是半天,津津有味,乐此不疲。现在能记起书名的,也是人们常见的几种,如《红灯记》、《白毛女》、《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剑》等等。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白毛女》、《铁道游击队》和《林海雪原》,不知是谁画的,线条流畅,雪景特别美,似棉花又似白云;每个人所穿的衣服,厚嘟嘟的,典型的中国农村装束,有一种温暖感。以致多少年后,我在自己遐想的各种场景里,都设想自己置身在那样的大雪里,穿着那样的衣服,挂着二十响驳壳枪,在飞驰的火车上身轻如燕,在茫茫的林海雪原上凌波而行。伴着这些连环画,我悄然度过了我的童年。在每次现在已不知什么原因的长途跋涉里,正是这样的遐想,使我忘记路途的遥远和行走的艰辛,给伤感的心灵带来了一丝安慰。后来,也不知怎么着,这些书都不存在了。只是在偶尔的沉思和不经意的梦中,突然悄悄地出现,将某一根神经撞得轻轻发颤。 小时候那些年代,不知是缺书,还是我们自己缺钱,总之是书很少,一直满足不了自己读书的****。有时为了看上一本书,替人推磨子拉粪,汗流浃背,不遗余力,好话多多奉承,笑脸多多相送,以期博得人的好感。更有甚者跑个七里、八里,翻山越岭,也只是为了借人区区一本小书。那时虽然是小小年纪,但每天在拔草喂猪、抬水挑粪之余,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能碰见的每一段文字。没有书,就读糊在墙上的报纸,读买东西时作为包裹用的报纸。王愿坚的《粮食》,就是我偶尔点着油灯从糊在炕头上的报纸上读到的,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故事就在心中那么晃悠悠地悬着,一直悬了好多年。跟着大人串亲戚,大人们坐着拉家常,烟雾腾腾,笑声朗朗,我则在一边偷偷地东察西看。一会儿冻得浑身哆嗦,鼻涕眼泪乱淌,大人就骂一声:“乱跑啥!”一把抱起搡在炕角。这时就默默地把头凑到墙上,一篇一篇地看墙报,看到深沉处,一时间竟不知置身何处! 但即使是那样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慢慢地我也有了自己的图书。有时父亲给了点零花钱,就一点点地攒起来,逢集的日子,兴兴地跑到街市上,隔着供销社的玻璃柜台,怯怯地买一本比较便宜的书。那时的书现在看来真是便宜,连环画几分钱,一本小说也只是两三毛。大人给了两根麻花钱,回家时就可以抱一本喜爱的小说。按捺着激动的心跳,从营业员手里接过发着油墨香的崭新的书来,急急忙忙寻一个人少的角落,一屁股坐下来,就再也不知什么日月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