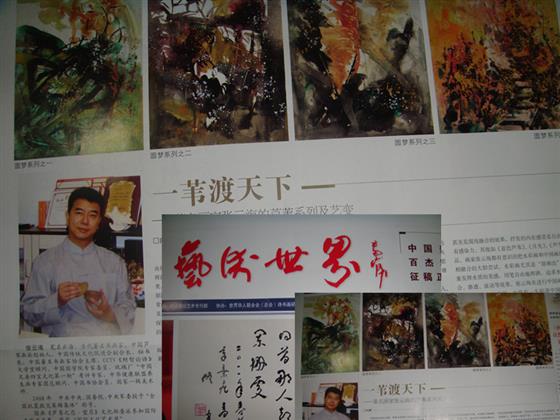
一苇渡天下
——画家张云海的芦苇系列及艺变
●向隽
(原刊于《艺术世界》2014总第64期)一些画家的成长过程,常常会有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由原来多种题材的绘画,会逐渐把兴趣聚焦于某一类物像的挥洒;二是表现形式和手法,会由某个画种演变到另一个门类,或者,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变。这里有艺术趣味扭转的原因,也会是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当然,还可能有更不寻常的由来,而其结果不一定都是理想的变局,有的画家在变化中确实得到了一回价值提升,有的反而艺术水平出现今不如昔的滑坡。我所以最先言及以上艺术之变,是因为画家张云海的创作,他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艺术求变者,其势态呈现的是欣欣向荣,是艺术境界的清晰跨越。
通观画家张云海的艺术创作,有两大值得关注的变化,而每一个方面的变化,都有着质的响亮释放,可以看作是更新的艺术转身。
张云海,慷慨钟情于芦苇的歌者
体验繁华而至沉淀之后是心态的清明烛照,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把过去对其他物像的理解转注于芦苇的尽兴表现,这是他的第一个变化。我所了解的画家张云海,之前的兴趣相当广泛,他不仅画了许多家乡皖南的风景,也因为当兵的缘故而画过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时代风采,更画过佛光照耀的禅境。有的具象生动,有的近似抽象的激情喷张,印象中,他画的茶马古道系列,把四季更替中情感的亦真亦幻弄得观者不由得心向往之。悄然之间,我们发现张云海的画面渐渐不再那么热闹多样,而是把一个最平凡的植物,变成了画笔下一再塑造的主角,这就是“芦苇”。有媒体报道他时,赫然曰为“中国芦苇画派创始人”,可见他的志向多么明确,甚至已经发力探索到一种痴迷的地步,他画的芦苇作品也的确成为拍卖行上实现交易最具关注点的题材。
那么我们还是好奇,芦苇,为什么迥然成为张云海如今创作的美术之眼了?我注意到他曾经说过学习传统和师法自然的话题,我想芦苇对他的情感促发也许更自然深切,乃至不画不快,由此可断张云海是难舍芦苇啊。
芦苇,曾经相伴我国的乡村文化或者田园文化走过了很多古典世纪,唐末的画僧贯休法师《秋末入匡山船行八首》所谓:“芦苇深花里,渔歌一曲长。”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美好意象,而画家的家乡就是芦苇养人的好地方,想来,张云海在文化传承上当是心挂芦苇且深谙芦苇之美的。
芦苇,是最早进入我国文学典籍的文学形象,“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2500年以前《诗经•国风•秦风》里的名句。张云海的书法也这样写过,芦苇是普通人喜爱的文学形象,他在一枝一叶的描绘时,也就传达出自己谦恭不让的芦苇情怀。
而现在我看到的芦苇,已经是张云海独特理解后的芦苇形象。对芦苇,他慷慨激昂,对芦苇,他钟情款款。
我说他是芦苇的钟情者,是解读画面后的判断,那里是一管芦苇挑起的静谧,是芦苇如林的豪阔气度,是艳阳送暖时的温厚秋意,是月洒芦花时的银光乍泄,比如张云海画的芦苇长条《温暖我心》,芦苇三竿,前后两竿举着仿佛如火在烧的芦花,中间是一竿墨色深重的芦花,节奏明快,雪意点题,表达了他对自然对人生的爱恋和赞美,不钟情者,难有此境。
唐代的孟棨《〈本事诗〉序》中说到钟情:“著於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说的是书香和诗兴,而张云海也是触事兴咏,他是用画笔作“咏”,咏的是芦苇一丛诗意轻扬,咏的是放逸自然时的殷殷钟情,咏的是感怀时代气象的画意勃发。
我说他是芦苇的慷慨歌者,有两方面的表现,张云海其人,说起自己画的芦苇来,宛如赞美恋人一般声调高亢激越;画起芦苇,则是不惜笔墨,小到斗方,大到横幅巨制,用笔时纵横施墨,敷色时泼彩豪爽,他特别喜爱画雪意覆盖下的芦苇,最典型的是34×136cm的《风花雪色那一世》,风雪弥漫中,双舟泊岸,而前景中的芦苇是竿挺精神,芦叶若旗,中景画的芦花则是欢舞荡漾,远景上是俊鸟竸飞,果然是一派呵护与捍卫的长歌大调,这样的画面会使人随之变得慷慨激昂,将自己化入其中。
因钟情而慷慨,因慷慨而放歌,读解这些芦苇作品,我们可以理解张云海为什么把芦苇画得那么如醉如痴了。
张云海,探索新境界的芦苇艺术家
不拘泥于某一门类的羁绊,唯思想情感的表达是取,在创作形式的选择上,把过去熟稔的西画技法融合进中国品质的笔墨形式,“改行”画起了彩墨芦苇,这是他的第二个突出变化。熟知张云海的都感到愕然,原来他是画水彩画的,也很擅长油画,怎么就画起了中国画?我想,还是与他热爱芦苇热衷于画芦苇有关,最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中国画最能够体现他对中国文化意境的理解,在他早期的水彩画中已经体现出这种写意为妙的审美追求。在我国南北朝时期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的“六法”中,有所谓“气韵生动、骨法用笔”之论 ,张云海是深研不懈的,在书法的习练中,他也在思考中国画的独到之处,毛笔用书写的意象线条更适合画芦苇的竿和芦叶,且泼法和破墨等技法也能够自由地表现墨色交融的韵味,我们来看《激情与缤纷》这幅作品,依然是芦苇浩荡,却不是具象的描述,而是对激情与缤纷的瞬间爆发的美感捕捉,事实上这是一幅带有鲜明西画特征的画面,西画比较重视环境的衬托,而传统中国画则讲究留白,所谓“计白当黑”,张云海的这幅画与他的大量芦苇画相似,都是在西画的功底彰显之下强调了环境气氛的渲染,其芦苇形象似是而非,只是让动感强烈的芦苇以更为意象,或者是有些抽象的形态在画面中与泼色互相交织飞舞,获得了得意忘形的甚至是混沌融合的效果,抒发的内在感受是自由豪放的,很有感染力。其他如《蓝色芦苇》、《月光》、《芦苇之恋》等作品,画家张云海都有意识的把水彩画和中国画的技法进行互相融合的大胆尝试。水彩画尤其是“湿画法”,其特点是注重发挥水质的美感,用笔自由地挥洒,追求水与色的相互融合、渗透、流动等效果,张云海在进行中国画转型时,没有忽略这个技法的应用,也没有一头陷进中国水墨画的规范,而是偏重彩墨写意画对色彩与墨的关系的探索,同时也耐心地探索了对光在景物上的中国画式的意写,其成功的标志就是对意境的把握得当,见线见骨,不失为写意精神为核心的中国气派。我们应该肯定这种艺术气魄,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敢画敢为,才能使中国画出现蓬勃生机。
张云海,一苇渡天下的理想主义者
我们讲,芦苇是最早体现中国诗歌美学即诗意的文学形象,芦苇还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指代作用,这就是芦苇的禅学象征,是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禅家符号,唐宋时代既有大量有关芦苇的禅意诗词留存下来。由此看出,芦苇在形成中国禅学的发生之初,更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最著名的还是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的传说。明代万历年间金忠士的《达摩面壁诗》有诗曰“渡江一苇浪花飞,九载跏趺坐翠微。”说的就是“一苇渡江”的故事,关于达摩“一苇渡江”的意义,在此不必多解。回到画家张云海,在与我交流他的艺术活动时表示,他不仅要画好芦苇,创造他的“中国芦苇画派”,还要努力让他笔下的芦苇艺术服务于造福社会大众的公益事业。我了解,张云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的负责人之一,近年来参与组织并举办了一些慈善的公益活动,为环境保护付出了不少实在的工作努力。从佛学文化考察,“一苇渡江”是因为映照合乎禅宗的机缘,而“一苇渡天下”则是新的使命,渡人至善,渡天下至大同,画家张云海要追求这样一个芦苇的境界,他用自己的芦苇艺术奉献环境保护的公益行动,他画芦苇,颂扬芦苇包含的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喝彩的,这样的苇业是美好的,用大爱的情怀来实践一苇渡天下的理想,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芦苇意象的时代变化。
2014/8/18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