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配合“达吉_雅娜的博客·繁体版与简体版之比较”重读了齐邦媛教授所著《巨流河》部分章节。下图即本人捧读《巨流河》一书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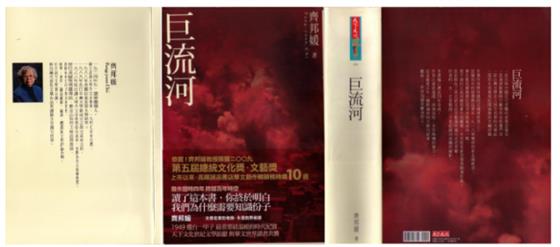
2009.7.7. 第1版 2009.9.30第7次印行 封面外加包纸图样 整书重量950克
这是一本须要“心态客观;虔诚理智;慈爱灵魂”才能接纳并读得懂的纪实性书籍。
缘由从网上拷贝“达吉_雅娜的博客·繁体版与简体版之比较”共有(8)篇,依次序“浏览”如下:
达吉_雅娜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guyana1130 转载 ▼
▼
《巨流河》繁体版与简体版之比较(1) (2011-11-06 16:35:57)
先读的是简体版的《巨流河》。之后听网友说,网上有台湾版繁体版的《巨流河》。淘到手后,发现厚厚长达600页。封面是庄严沉重的绛红色,宛如封尘已久的血色。
翻开竖版的繁体字,从容流畅的叙述,有一种雍容的文字魅力。
“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只这一点,在我生活的大陆就比较稀缺。何谓“人的样子”?在愚民与谎言的双重灌输下,多少人不知何谓人的样子。
作者在第二章“血泪流离”中,回忆抗战的烽火年代:“……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们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愛,尤其是自尊与自信。”
——献身,是母性中的一部分;爱,则是人性中至善至美的情感;可惜我们几代人,已经罕见这样的教育。回顾童年迄今,我竟然从未见到生活的这个世间,听到或者感受到这种教育……情感教育的断裂,已经让我们难以回归正常了。
“自尊与自信”,几代人稀缺的品质啊!
读到“南开精神化身”的张伯苓在抗日时期的故事,我唏嘘不已。……时至今日,何处寻觅这样发挥巨大能量的伟大教育家?虽然我们并不缺优秀的教育家,但他们要么被强迫“赋闲”在家,要么就是被流放疆外。
开卷篇删减的,全部是最能体现作者个性魅力的灵动文字。按照大陆审视文化的标准,这的确是以消灭“鲜活的个性“为己任。想想自己执着了十余①载的文学梦,不由心寒如冰。要知道,出版简体版《巨流河》的出版社,可是大陆鼎鼎大名的三联书店。难道连国家一流的出版社都被几十年的极权文化所侵蚀了么?那么,文学的出路在哪儿……,或者,连这个提问都是多余?这难道就是大陆文学的真相么?
以下是删减的第一段落:(摘自台湾的繁体版《巨流河》第9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权,正面抗日的国民党军民,侥幸生存在大陆的必须否定过去一切。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备‚湮没(与ƒ)遗忘了。”
“六十年来,我沉迷于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打气,却几乎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它们是比个人生命更庞大的存在,我不能也不愿将它们切割成零星片段,掛在必朽的枯枝上,我必须倾全心之虔诚才配作此大叙述——抗战中,奔往重庆那些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那些在极端悲愤中守护尊严的人:来台初期,单纯洁净为建设台湾而献身的人。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的青年、中年也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父母已逝,哥哥与小妹早已移居海外,在台湾只剩下我与宁妹二人,这些年中,总有像相依为命之感。只有她深切了解,此书未写我将死不瞑目。今年开春,为了庆贺我书写将成,她开车带我上大屯山主峰,左望淡水海湾,右眺台北四周群山。人生至此,何等开阔!
而我的丈夫裕昌。如果不是被病情困住,他对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些艰难那些苦楚,该有多少感慨!愿我们的三个儿子,能分享我完成此书时的快乐。”
——这段充满温馨生命情感的文字,为何也被删?难道也“无用”么?
以后的文字,多处修改。然而我还是喜欢台版的“序”,因为有着作者独特的精神世界与气质。文字未必需要符合什么。真实、性情就好。
【注】
① 余,宜作“餘”的简化字“馀”。下同。
② 备,“被”之误。
③ 与,原文有“與”。
《巨流河》繁体版与简体版之比较(2)(2011-11-07 19:24:54) 转载▼
第二章“血泪流离”
台版第77页被删减的文字:
“莽撞粗鲁的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损伤了东北军的形象,给延安中共日后壮大的生机,将中国人抗日的热情更集中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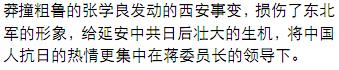
台版第139页至140页被删减的文字如下:
“……2002年左右,我突然在台北书市看到这本书(指前苏联作品《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早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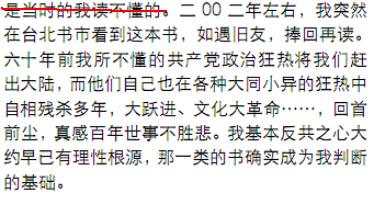
第149页第一自然段“永别母校”
“……她们竟然还记得中学时代的那种爱情向往。……(删减如下)当年黑暗宿舍中的少女,怎样走进政治风暴又如何从文革脱身,我都不敢详问。”
简体版第135页(台版的第218页第三自然段被删减文字如下)
“……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个困惑。日本与德国在盟国的扶助下迅速复兴,而中国国军却在战后,疲兵残将未及喘息,被迫投入中共夺取政权的内战,连‘瓦全’的最低幸福都未享到。”
在简体版《巨流河》第138页(繁体版第224页),开头便有着大段的删减。
战后新局——失落的开始
在举国欢腾的那几天,我父亲竟然常常深锁眉头,沉思不语。
有一天在晚餐桌上,他对几位老友说,苏俄在停战前五天抢着对日宣战,立刻就越过边界攻入我国满洲里,深入东北境内百馀公里,十天内占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俘虏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史(斯)达林① 在八月二十三日宣称:“满洲国全部解放”,完全不顾我国的政治主权。中共的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连发七道命令,指示共军全面发动,争城夺地。并命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及若干朝鲜人,率人开赴东北,配合苏俄军作战,先夺东北三省。
然而,毛泽东却在一个月后的九一八纪念日来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对蒋主席邀其前来重庆表示感激,致辞说:“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之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杜绝内争,因此各党派应在国家一定方针之下,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之新中国。”
这是我今生听到的最大谎言之一。
繁体版《巨流河》第227页:
“……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以下是删文)二十年后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利用这种划分方式作为残酷斗争的根据,隔着台湾海峡所听到的一鳞半爪,和在海外读到的铁幕消息,都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
第235页
“学潮在全国各大学扩散,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大学校园充满了政治动荡叫嚣,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占据全国,之后的四十年,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成为政治工具,学术传授及专业标准近于切断。”
【注】
① 史达林,既然繁体字都改为简化字,“史达林”改作“斯大林”字为宜。
《巨流河》繁体版与简体版之比较(3) (2011-11-08 20:02:59) 转载▼
台版《巨流河》读到小半,也就是第238页时,有一段删减最大的段落。如下:
“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激① 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我常想闻一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共产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闻一多》一书记载,他的遗物中有一枚没有刻完的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无论怎么诠释,说是他在生死关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这枚“自励章”表白心志,决心以“追屈原、拜伦踪迹的莊严表示”作最后的遗言,正常的读者很难不联想到懊悔与自谴: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情深意明的好诗,深研过文学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的意义的。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庭换来幸福。
一九四五年的中央政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的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民死於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入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了”的境况?
这是多年来我回想在四川、武汉多次被迫参加游行时,内心最大的困惑与悲愤。
《最后的乐山》台版第242页
“张莘夫是工程专家,原为我父亲东北地下抗日同志,胜利后被派由重庆回辽宁接收全国最大的抚顺煤矿,一月十六日赴沈阳途中,被共军由火车上绑至雪地,同行八人全被残杀。俄共迅速拆迁东北大型工厂的机器,每迁出一地即协助中共军队进驻。这是继去年十一月底响应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发动的反对内战,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的游行后,第二次全国性学潮。同学中政治立场鲜明的,积极组织活动,口号中充满强烈的对立。游行的队伍挤塞在一九三九(年‚)大轰炸后仍未修建的残破道路上,路窄得各种旗帜都飘不起来,只听见喊至嘶哑的各种口号,‘打倒……打倒……万岁!!……万岁!!’自此以后,隔不了多久就有游行,只是换了打倒的对象,除了经常有的“中华民国万岁”之外,还有别的万岁,每次换换即是。”
台版第249页末:
“……但是我有时会在尘世喧扰中想到他们那种可羡的活法。中共当权之后,他们可能逃不了迫害吧。可悲的中国人,常常不能选择自己的活法。”
台版第260页被删减的句子:
“……并将日军五十九万四千人全部俘走,宣称‘满洲全部解放。’胜利后一整年,抢迁境内工业设备运往俄国,将重要地区、港口、军事设备交给中国共军,帮助他们与中央军对抗。……”
台版第275页末段被删减文字:
“……繆教授的课演变成三分之一文学,三分之一ƒ政治。他的文学攻击语言配合戏剧性动作,在中共由敌后到公开的攻城多④地开始⑤之时找到了着力点。更具有煽动力。外文系师资刚复员武汉还不够充实时,他的舞台扩张至全校。那是一种潮流。”
(台版第277 页第一⑥行倒数十一、十二字“共军”,在简版中变为“共产党军队”)
台版第279页最后一段被删减的文字:
“……执行捕人开枪者严办。武大六一惨案成了中共夺取政权的一大文化武器,然而二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惨死的无数大学师生,又该如何控诉?”
【注】
① 激,原文作“热”。
② 年,原文有“年”。
③ 一,“二”之误。
④ 多,“夺”字误。
⑤ 开始,原文有的。
⑥ 277,原文在276页第十七行。或许另外版本是在“第277 页第一⑥行倒数十一、十二字”的可能。
《巨流河》繁体版与简体版之比较(4) (2011-11-09 21:14:12) 转载▼
台版第403页被删减文字如下:
“……民国六十年以后,在外交的逆境中,台湾靠自己的奋斗创出了经济的奇迹,得以在国际扬眉吐气。可是在国际文坛上,我们却几乎是暗①哑无声!有些人讥嘲台湾是文化沙漠,而我们竟无以自辩!实际上,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坛除了抗议文学和备受攻击的朦胧诗外,可说是寒蝉世界;而台湾的文学创作,由于题材和内容形式的多样性,却有自然的成长,无论是写实或纯艺术性的作品,反映的是政治不挂帅的真实人生。”
台版第407② 页的第二自然段,是作者叙述与学生之间的真挚友谊。这可非“等闲”之笔,实乃人性至情的体现。然而大陆的文化审美,显然已不具备正常的“审美”了。正所谓:愚蠢者,却不知愚蠢为何物。
“在那个没有电脑的时代,我幸有一位得力可靠的助手莊婉玲秘书。当我决定到编译馆时,在中兴大学外文系第一班毕业生中,我选她,因为她写字端丽,性情温婉,为人稳重和悦。她以资聘秘书职帮助我与馆中同事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我在工作上、精神上都倚重她甚深。那时报上连载漫画(安全杆是什么?)有一天登出一则:“安全杆就是我说什么,你听什么。”我拿给她看,两人相视而笑。在险恶的环境中,她是我很大的安慰。选集完成后,她结婚随夫赴美定居。直到两年后我自己也离职,她走后无法补上的空座,令我怀念师生共同工作的日子。”
台版第430页被删减文字:
“我记得后来一次谈到文革红卫兵对师长和文化人的摧残,待这批人长大,统治中国,他们的暴戾人性会将中国带到何处去?我深以为忧。……”
——我以为:这应该就是指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他们以自身的学识和素养,看透每件重大事件背后所蕴藏的真相。这也正是统治者最害怕的事情。
台版第431页
“……一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机③,顾虑甚④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
台版第477页至478页被删减的文字:
“……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九那些年,许多听众总是会先问:‘你们在非洲吗?’‘你来自有金佛寺的泰国吧?’自此以后,我在国外公众场合,尽量穿矮领,自然宽松,下摆开叉在膝盖下,走路毫不局限的旗袍,绝不戴帽子,至少不要被误认作日本人。在最早的交换计划中,美国人似乎比蒋总统更实践‘以德报怨’的主张,我第一次去访问时,同期竟然有四个日本人!而我代表‘中华民国’却只有一个人,一直是孤单⑤奋战。所以我必须努力保持国家的尊严,‘输人不输阵’。”
台版第479页被删减的文字:
“我胆敢主编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另一个信心也来自两次访美期间,我在密西根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那样有规模的图书馆搜寻询问,都没有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两校都开设不错的中国文<学⑥>史课程,虽然也有少数亲共学者努力帮中共说‘解放’的好话,但多数学者指着书架上一排中共建国后的样板文学,如《向雷锋学习》、浩然《金光大道》、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舍《龙须沟》等,说道:‘中共虽然紧闭铁幕,但是他们政治斗争之无情,人民生活之艰苦悲惨仍是举世皆知的。我们能在这里的教室宣传这些歌功颂德的宣传文学⑦吗?怎么对美国学生解说这些谎言呢?’然后,他们转换话题问我:‘台湾有文学吗?’”
接着第二段(第480页开头)“……编纂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时,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共同的定位。因为发行者是国立编译馆,所以选取作品必须有全民代表性,编选公平,不可偏倚遗漏。我们五人小组中,何欣和余光中参加台湾文坛活动最早,拥有台湾文学的资料最丰富。我自回台北后,阅读重要作品甚少疏漏。开始教‘高级英文’后,更是勤跑书店,新出版的书尽在掌握之中,和在美国读书时一样,可以跟上时代阅读重要作家的研究。从那年起,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渐渐有相当齐全的台湾文学作品。譬如黄春明的《锣》,扉页有作者写给我的话,就和《英国文学史》八世纪第一篇初民史诗《贝尔伍夫》并排而放;司马中原《荒原》、《黎明列车》与朱西甯《破晓时分》、白先勇《台北人》,这些初版与一九六、七零年代的小说随我自上海带来雪莱、济慈全集的珍藏本并列齐观。我曾经相当欣赏年轻女作家萧飒,她所有的小说则和薇拉·凯瑟、舍伍德·安德许、伯那·玛拉末等美国作家作品并肩而立。我往返於两种文字,乐在其中,有助於我写评论文章的视野与层次。
【注】
① 暗(an),原文作“喑(yin)”。
② 407,原文在406页。
③ 机,原文“计”。
④ 甚,原文“实”字。
⑤ 单,原“军”字。
⑥ 学,衍。
⑦ 学,原“字”字。
《巨流河》繁体版与简体版之比较(5) (2011-11-11 20:14:45) 转载▼
“两岸文学初相逢的冲击”一文中的大段删减(台版第484页),应是当前意识形态刻意回避的话题。其内容未必涉及不同立场、观点。它透露的真相,有助于提升人的判断力,恢复理性思考。——这才是删减的原因。
“自英译选集之后,我在世界各处开了许多大型的文学会议,在圣约翰大学这场真正的群英大会,我第一次看到政治的炎凉如何移转到文学界的炎凉,也第一次看到了文革的厉害,进而促使我以宏观角度省思‘台湾文学’的定位与定名。
那(真①)是一场盛宴啊!所有人都很兴奋,所有的眼睛,所有的耳朵都充满了好奇,专注於首次在西方世界现身的铁幕作家身上。中午吃饭,我被安排与他们同桌,大约是象征两岸交流,而我看起来是最没有战斗精神的人吧!首次见到对岸的人,都不知道问题从何问起才好,他们知我家乡在东三省,说:‘回祖国看看吧!’大家只好傻笑。夏志清兴致很高,他说:‘你们到了美国,多看看吧!’
午餐后回到会场,正在听大陆作家一篇文坛近况报告,突然会场门口一阵喧哗,在一大群人推推拉拉制止不住的混乱中,奔进来一个高大漂亮的年轻中国人,他直朝大陆作家冲去,大声喊叫:‘你怎么好意思代表那个暴政到此讲话?’接着占据了讲台,嘶吼喊叫控诉文革的残酷。主办的师生好不容易把他拉到门外,他在门外还骂了一阵才被劝走。大家惊魂甫定才知道,这年轻人即是那时在西方世界畅销,揭露大陆文革惨相,《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他与共同作者夏竹丽结婚得到美国政治庇护,得以英文写完并出版此书。《革命之子》叙述文革的种种暴行,使西方世界看到大陆几成人间地狱,那些红卫兵之凶狠无人性,令读者寒慄,血脉喷②张。我读时悲愤地想:这是我念念不忘的祖国吗?
赶走了闹场的人,会场气氛已变,最初单纯的兴奋与好奇被破坏了,早上各种立场的演讲与所营造的表面平静都不见了。尽管讲台上照程序进行论文宣读与讲评,台下的人多在悄声讨论刚才闹场者的背景和他的控诉,大家对表情尴尬的大陆代表的好奇心就更复杂了。当时,二次大战后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新一代的‘汉学家’几乎都在场,他们怎么想?而我,在离开大陆三十多年后,第一次看到铁幕后的真人真事,内心激荡,好似看到一片历史真相的实况,不是任何电影或文字所能呈现的真实,令人伤心。
会后我在纽约停留数日。一天晚上,我台大的学生,《中国时报》记者林馨琴邀约晚餐,在座六人,有两位就是《革命之子》的作者。饭后受邀到他们的小公寓,谈到深夜。他由静静的叙述转为激动,有些书中未载的情景,人对人无法言说的背叛与残暴,令听者岂止惊骇落泪而已。是什么样的警醒力量,使这二十多岁的红卫兵在那样血/腥的浪潮中,游向人性的岸边,对自己参与的暴行提出控诉?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真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
夏天的夜晚,走在纽约街头,真不知人间何世!我清晰地忆起自己二十岁的时候,躺在武大女生宿舍阁楼的斗室中,仰望满天的星斗,在三江汇流的水声中,为侯姐姐骂我没有灵魂而流泪,只因为我不愿意随她再去读书会,读那些俄国阶级斗争的书,唱那些幼稚的‘东方红,东方出了个***,……’我记得在乐山狭窄的街上,学潮队伍中仇恨的口号和扭曲的面孔。一九四七年,我若没有来到台大看到那两屋子书而留下来,我的人生会是怎么个样子?
那些年在西方,同样令人震惊的文革真相名著还有西蒙列斯《中国大陆的阴影》和白礼博《来自地心》等,大陆的‘伤痕文学’到台湾出版,又是多年之后了。”
【注】
① (真),原文有“真”字。
② 喷,原文是“贲”。
《巨流河》繁体版与简体版之比较(6)(2011-11-13 19:04:48) 转载▼
在“译介台湾文学的桥梁——中华民国笔会”一文中,起始一段(第498页)
“我既是做学术交流的人,必须先站稳台湾文学的立足点。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经验之后,我得以从美国以外的大框架欧洲,思索台湾文学已有的格局和未来的发展。……
台版第502至503页的大段删减,可能编辑认为个人经历的故事(对台湾文学所做的贡献),不足为道?如果台湾真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此人怎可能不重要?为完整性,虽然第一自然段的台版与大陆版皆有,我还是予以保留。如下:
“殷张兰熙金发碧眼的美丽母亲,一九一七年嫁给中国同学张承槱先生(来台后曾任审计长),由美国维吉尼亚州到中国湖北县城成家,生儿育女。十多年后兰熙长大,毕业於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一九四九年随夫婿殷之浩先生来台湾,创立大陆工程公司,因为出国开会而冠夫姓,文坛好友都只称Nancy。她爱文学,有时也写诗,一九七一年曾出版One Leaf Falls诗集。(此段台版与大陆版皆有)
一九七二年我从台中搬到台北,恰巧与兰熙住在邻巷,街头遛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编笔会季刊和《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最基本的话题是值得译介的书稿,英译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译文,整体的安排,呈现的效果,国际读者的反应等等,好似长河流水,永不厌倦。
兰熙是个开朗温暖的人,忙碌中热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开的年会前,催集论文,安排演讲和讨论议题,准备礼物,到会场结交天下士,握住那么多伸出的友谊之手。大陆的‘中国笔会’文革后参加总会,多次在会场排挤我们,兰熙收起她自然温婉的笑容,登台发言愤慨迎击,保卫自由民主的台湾代表权。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他们不再出席年会。在今日政局情势下,会籍立场仍会被提出,但是兰熙与当年代表所建立的国际友谊,以及我们的季刊三十多年稳定的出刊,丰富的专业形象,已让中华民国笔会立于於不易撼动的地位。中美断交后,兰熙受邀在美国十家地方电视台上‘谈台湾’(‘Talk about Taiwan’)节目。侃侃而谈,以条理的分析,清晰的言辞,呈现台湾在文化、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英文的笔会季刊更帮助增加了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为台湾发声的事,兰熙做了很多,但是在台湾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贵的是,这些奉献和她主编笔会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仅有外交部和新闻局所付国际赠送的那数百册书款,国内在诚品等地出售则不及百册,主要的支出如稿费、印刷、发行及人事费用,皆由殷先生资助。笔会会址原也设在大陆工程公司所在地,殷先生去世后,一九九六年开始租屋在温州街,即将面临断炊时,殷氏‘浩然基金会’开始资助,得以编印发行至今。”
台版第506页末段至508页被删减的文字:
“孟瑶自以《心园》成名以后,二十年间有四十多本小说问世,书店都以显著地位摆着她的新书,如《浮云白日》、《这一代》、《磨剑》等,相当受读者欢迎。一九八四年,我写了一篇《江河汇集成海的六O年代小说》分析:‘这些篇小说的题材都来自现实人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生老聚散的人生悲喜剧。孟瑶擅写对话,在流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一些代表人物对世事变迁的态度。她小说中的角色塑造以女子见长,多是一种独立性格的人,在种种故事的发展中保有静静的刚强。’也许是她写得太多了,大多是讲了故事,无暇深入,心思意念散漫各书,缺少凝聚的力量,难於产生震撼人心之作。多年来我仍希望,在今日多所台湾文学系所中会有研究生以孟瑶为题,梳理她的作品,找出一九五O至七O年间一幅幅台湾社会的人生现象,可能是有价值的。因为她是以知识分子积极肯定的态度写作,应有时代的代表性。
潘人木和孟瑶几乎是同时在抗战时期毕业於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前者是外交系,后者是历史系。潘人木惜墨如金,《涟漪表妹》一出版即得《文艺创作》月刊社征文的二奖,虽是‘反共小说’,却以真正的沉痛写抗战时期青年的愤怒和狂热,政治的巨浪在一个女孩人生举步之际卷走了她,淹没了她的青春,失身、失学、远走延安,再归来已家破人亡。过了三十年再写《马兰的故事》,以精炼的文字写乡土风光。人物内心的反响,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故事虽不浓烈,全书却是艺术之作。她后来继唯一的短篇小说集《哀乐小天地》之后,十年间只创作一、二篇短篇小说,但是一九八六年的‘有情袜’以及二OO六年逝世前两个月创作的‘一关难渡’,堪称艺术精品。
我从台中‘进城’到台北之前,反共小说的政治高潮已过,但是我仍赶上尾声,对于张爱玲《秧歌》、陈纪滢《荻村传》和姜贵《旋风》有及时的认识。其实,对于他们的时代记忆犹新的人仍多,我自己也从那天地中出来,所以能虔心诚意地写我那篇‘千年之泪’和‘时代的声音’。姜贵来台湾时已五十岁,经商失败,妻子久病去世,生活困顿,在真正的家破人亡的创痛中以大叙述之笔,错综复杂地描写从‘五四’时期到抗战初期,一个山东大家族在共产党窜起之际的兴衰,他的《旋风》和《重阳》必能传世。近半世纪后,此书由九歌出版社重印,我曾写‘旋风中的绣花鞋’详述我对传统中女子的处境最强烈的反思,可是历史上的斑斑血迹,已非今日女性主义者的课题,后来也无暇再作进一步研究。王鼎钧的小说《碎琉璃》和散文集《左心房漩涡》是我这一代最精美深刻的文学怀乡作品。他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二OO九年三月刚出版的《文学江湖》,真是文人一生梦寐思念得以完成的磅礴力作,也只有王鼎钧的才会①和坚强性格才能完成。和记述一九四九年前后苦难的早期出版的王蓝的《蓝与黑》、赵滋番的《半下流社会》、彭歌的《黑色的泪》、纪刚的《滚滚辽河》,都是传世之作。”
【注】
① 会,原文是“华”字。
《巨流河》繁体版与简体版之比较(7) (2011-11-17 21:49:47) 转载▼
台版第513页删减如下:
“以前只之多① 兰熙经常用殷之浩先生支票付款,我接编后,殷先生病中,尚主动送五十万元至季刊,宣扬文学成就。政治和文化政治刊物,有新闻局、外交部每期买数百本赠送友邦,戋戋书款便是我们全部的收入。文建会有一位颇为‘同情’的专员私下指点我们,可以‘文化遗产专栏’计划前往申请补助,所以我请曾上过我台大‘高级英文’班的艺术史组的学生颜娟英和陈芳妹,轮流为季刊每期写一篇英文论文。颜娟英在哈佛得学位,回国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由‘唐代佛教之美’写起;陈芳妹在伦敦大学得学位,回国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由‘国家垂器——商周贵族的青铜艺术’开端,一直写了十年,助季刊得到文建会辅助印刷费。
最艰困时,好友文月代为申请得到她的父亲‘林伯奏先生基金会’辅助部分稿费等。有两次助理月薪发不出来,隐地私人捐助度过难关。笔会有一个堂皇的理事会,定期开会而已,对于我实际的困境,只说‘能者多劳吧!’聚餐结束各自回到舒适的本职。我满七十岁的时候,实在身心俱疲,请理事会务必找人接替,他们嘻嘻哈哈地说:‘你做得很好呀,人生七十才开始啊。’说完又散会了。”
台版第514页“……我接任主编后,他(指康士林教授)是我最可靠的译者与定稿润饰者,我所写的每期编者的话都请他过目。日后我经手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译的书里书外,他也都是我第一位读者(英文‘reader’,亦有‘校阅’之意)。近二十多年间,我们小自字斟句酌谈译文,大至读书、生活,一见面就谈不完。他知道我多年来以珍·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作床头书,身心得以舒展②,每到英美旅行、开会,常给我带回各种版本、录音、录影带。二OOO年我读到柯慈的新作《屈辱》,大为此书创意所吸引,坚持他抽空读一遍,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番。拥有真正的比较文学的文友,实在难得!”
台版第516页 “……其中吴敏嘉是我台大的学生,英译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杜南馨英译平路《行道天涯》,更於二OOO年和二OO六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当然,她们的才能并不是(只③)由研究所的教导,还因为随外交官父母在国王④长大,受完英文中学的教育,有很好的译成语言训练。回到台湾上大学外文系,兼修中国文学课程,最重要的是不仅爱文学,而且达到了相当的文字水准。
台大外文系在比较文学方面确实有一段黄金岁月,自一九八O年代后期,年轻的一代,如宋美璍、张汉良、彭镜禧、高天恩,受邀参加笔会,开始与我们出去‘跑天下’,写主题论文,开国际年会,协助并接受后来笔会季刊的编务。更年轻的后继者,则有郑秀暇、史嘉琳,以及现任总编辑梁欣荣。一群文学伙伴凝聚‘我们台湾文学很重要’的共识,并在不断延揽人才的过程中,结交了许多海内外英译高手,如葛浩文、闵福德、马悦然、奚密;尤其是陶忘机,以二十余岁之龄为季刊译诗。自一九八三年至今已翻译数百首台湾最好的新诗。”
台版第520页,第二自然段:
“在那许多年中,我当然知道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长篇小说的英译,就缺少了厚重的说服力。所以一九九O年,文建会主任委员郭为藩先生邀集‘中书外译计划’咨询委员会时,我欣然赴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出建议,大家开出待译的书单、可聘的译者和审查者。开会十多次,每次郭主委都亲自主持,认真倾听,讨论进行的方式,文建会也确实编列预算。突然郭先生调任教育部长,接下去五年内换了三位主任委员,每一位新任者都邀开同样的咨询会,但都由一个副主委主持,先把前任的会议记录研究一番,批评两句,修改一番,敷衍些‘谢谢诸位宝贵的高见’的小官僚话,然后散会。这样的会开到第三次,我问那位主持社区文化专家的副主委:‘为什么要重复讨论已经议定的事项?’他说:‘换了主委,游戏规则也得变。’我说:‘我很忙,不与人玩什么游戏。’站起来先走了。从此不再[拨冗]去开那种会,对台湾的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
从笔会季刊创刊起,我便是长年效力的顾问,但是自己太忙,从未过问它的实际业务,一担挑了近十年!那十年的得失怎么说呢?我一直在等待,观察恳求可能解救我的接班人,但是那是一个没有经费、没有编制、没有薪水、没有宣传,也没有掌声的奇怪工作。比我晚一代的好手,稍作考虑即感到这样的献身,甚至不知为谁而战,都说太忙而拒绝接手。事实上,我早该明白,撑着这本刊物是件超级寂寞的苦工,真正的作家都是‘单枪独行侠’。笔会原是以文会友的组织,但是兰熙退休后,她所建立的国际友情,如英、法等笔会原创人已渐渐凋零。
一年复一年,我对笔会季刊的感情好似由浅水一步步涉入深水,直至千禧年才得以解脱,不舍之心是有的,但是岁月不饶人,解脱就是解脱。我曾经背着轭头往前走,所完成的当然是一种堂⑤吉诃德的角色。”
【注】
① 之多,原文是“知道”二字。
② 展,原文是“适”。
③ (只),原文有“只”字。
④ 王,原文是“外”。
⑤ 堂,原文是“唐”。
pdf. 版 755~757页 校对重编 第 叁叁柒 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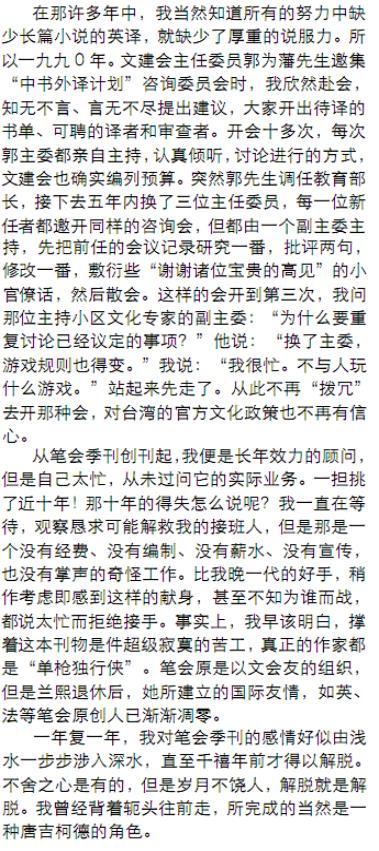
《巨流河》繁体版与简体版之比较(8) (2011-11-18 22:07:03) 转载▼
台版第526页,第二自然段:
“十年间我们用纸笔通信。在进步到传真机的时候,第一封传给德威的信,是一九九八年农历除夕写的:‘寒流正一波波袭来,窗外鞭炮声也比往年少些,据云不景气,凡事萧条……。’此信系为李乔《寒夜》英译出版而写。当时哥伦比亚大学请一位写稿人,认为《寒夜》对世界文学研究很有价值,但对一般英语读者或许‘不甚有趣’。我说,若有价值,就值得这个计划出版,从《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杀父①》的角度,《寒夜》和《亚细亚孤儿》等,当然‘无趣’,但是今年英、美两大奖得主,阿兰达蒂·洛伊《微物之神》和查尔斯·佛雷泽《冷山》也不甚有趣。就台/湾/文/学的发展来说,《寒夜》、《三脚马》和《千江有水千江月》这些长篇是我们所爱的(dear to us)。后来我在一个国际研讨会场发言时提到此点,有一位美国学者回应:‘你说:dear to us. 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我们] 啊!”
雾渐渐散的时候
二十世纪即将过尽之际,日历的撕翻,年历的更换,触动更敏锐的今昔之感,这漫长、苦难、漂泊的百年即将成为历史。我父母的那一代过去了,我自己的这一代也已是落日时分了。
一九九八年,评论集《雾渐渐散的时候》(九歌)即将出版时,我正在四访德国的旅途中,下榻波昂城外莱茵河上一座旅舍。我日夜坐在伸展到河上的凉台,在水声里写那篇自序。这本书是继《千年之泪》,阅读台/湾/文/学又一层的思索。前人因读杜甫<无家别>而落千年之泪,如今二十世纪将尽,一九四九年以前流离失所的泪已渐止,代之以今世的忧闷焦躁。这五十年来,我看着台/湾/文/学的发展,好似在国际文坛、国内变局重重的迷雾中行走,寻求定位。在整理书中文稿的时候,好似看到一些阳光照亮的土地,个人视野之内,雾随②不曾全散,终有渐渐消散的时候。这本书里有我费事费力编辑文选的几篇序文,也有我最关注的眷村文学和<二度漂流的文学>、<文学与情操>以及谈翻译等篇。在真正的世纪末那几年,政治的冷手已伸进了文学领域,纯真的爱与信赖已几乎全被放逐,作二度漂流了。
台版第529页,《鼓吹设立国家文学馆》一文中,被删减的文字如下:
“第二天上午是九歌出版(社③)二十周年庆祝会,原已邀我作‘贵宾致辞’,当晚我思索许久,决定在贺词之外,为这件事说一些话,这不该是我一个人的愤怒。这样的聚会就是真正的文坛之会,许多人已知我多年。我在会场详细说明自己与这件事的因缘和所耗时间和心血,唯一的期望是给我们的文学一个[家],绝不能与古籍、文物、保存技术等混在一起,在衙门的屋檐下挂一个孤零零④的牌子,收藏一些发黄的手稿。因为在台湾这样的政治环境,只有文学是超然的,或能不受政党、经济的影响。如果定名为国家文学馆,台湾未来是统是独,它有文学的尊严,任何搞政治的,也没有胆量推翻一个[国家]。我一场慷慨陈词不但引起与会文友的热烈反应,第二天四月一日,各报都有相当显著的报道。《联合报》文化版以很醒目的标题:‘不设国家文学馆——文学之耻’强调此馆之重要,并且附了一张我在麦克风前握拳大声疾呼的照片,以半版的篇幅写作家的发言,和设馆乖舛的筹备过程,反映了政治现实妥协下的荒谬……。
这些声音确实产生效果,不久我们即受到立法院几位文化立委和教育立委召开听证会的邀请函。我认为自己公开呼吁已说明了衷心盼望应该有更多的声音和力量,在会前我写了一封信给向阳……”
台版第546页,删减、更改的文字如下:“……那些年,布满东三省,一心一意跟着我十多年在敌后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他们盼望胜利的中央会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妇,也全落了空。没有出来的人,能在共/产/党/手里活着的也很少,那些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适应生存,养家糊⑤口,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这些话,他反反复复地说着,折磨着他最后的日子。”
台版第563页,少量的删减与更改:“第二天早上,车已过了鸭绿江,到了韩国的新义州车站,从此是暗无天日的生活,不断的血战,不断的转移,人只是个拿枪的机器,敌人是谁都不清楚,家乡当然不能联络。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官兵来台湾,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二三自由日’,这些义士给蒋总统的反共力量增加了很大的声势。”
pdf. 版 807、808 校对重编 第 叁陆零~叁陆壹 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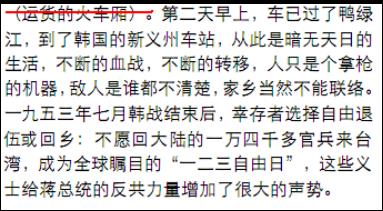
最后,选一段个人最喜欢的文字描述:那是恪守作者内心深处的,最纯粹纯净的爱情。(摘自《巨流河》台版第584页)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完》——
【注】
① 父,原文是“夫”字。
② 随,原文是“虽”。
③ (社),原文有“社”字。
④ 零零,原文是“伶伶”。
永陵按:
1、由于先前没有“简体版《巨流河》”可以参照,只是根据浏览“达吉_雅娜的博客·繁体版与简体版之比较”得出上述三十馀处 【注】。至于如:“韩/战”等等字间,为何加原文中所没有的斜杆杆?颇费解。
2、原版繁体直行排列有许多书名、人名下面附:湯瑪斯·曼《魔山》(Thomas mann,1875-1955, Der Zauberberg)
简体字版是否也都有附注出来? 如果没有,是否亦属于被“删减”之列?如果改动很多,是否可称谓“改编”版呢?!
3、发表拙文“读《巨流河》章节笔记暨校对“繁体版与简体版之比较”之误”只是说明本人再“读”了一回《巨流河》之佐证,并借机与大家分享读书的“心得与快乐”而已!
4、同时,在原文繁体版上尚没有发出现错别字!

黄永陵 于温州知省斋 谨上
该文粗成之时(2016.10.15. 0230),从网上下载了横排简化字“巨流河(台版)pdf”将会好好研读一番。
又及:达吉·雅那所指系三联书店出版蓝色封面的《巨流河》(余尚未读及)而11月 3日开始首发的拙稿
“校对简化字版《巨流河》暨重新编排之一”至今已经发了十二次,将于12.25发完全书(十五次)。
是根据佚名输入发到网上的“巨流河(台版)PDF. 3.2MB”文档基础上进行校对与重新编排的。
今(12.18)日下午特将达吉所提及被删除的段落,从“巨流河(台版)PDF. 3.2MB”中摘录四
段出来插附相应之下,以示说明!只是原版书中有“序、书前、书援”以及40幅照片被删除;讹误
多多 另行在拙稿第十五发的“后记”中会有说明。
2016.12.18 1900 黄永陵 于温州知省斋 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