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差异的可能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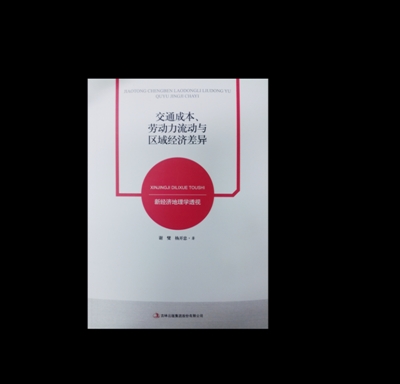 |
|
|
区域差异问题是各界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与交通运输大通道相关的跨区域运输成本的下降,对区域差异产生重要影响。谢燮、杨开忠所著的《交通成本、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差异》(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3月),运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方法,探讨了中国区域差异的可能走向。该模型引入了各种可控参数,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给出不同条件下中国区域差异的收敛或发散趋向,为区域政策提供理论的基点。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为首的西方经济学家将Dixit-Stiglitz模型的垄断竞争框架与萨缪尔森的“冰山交易技术”相融合,从而实现了主流经济学向地理空间的扩展。该方向被保罗·克鲁格曼等称为“新经济地理学”,其实质是Dixit-Stiglitz模型的空间版。2008年,克鲁格曼因为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创性成果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一轮热潮。
《交通成本、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差异》采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均衡模型方法,以我国沿海与内地的区域差异为背景,从中抽象出我国地区差异的特征事实,并将它们融入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从而为我国的区域差异现状及未来发展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该研究将劳动力分为高技术劳动力和低技术劳动力,将区域间高技术劳动力的流动、区域内低技术劳动力的城乡流动以及制造业的集聚所引致的区域差异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与一般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相类似,引入报酬递增的中间产品部门、报酬不变的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不同的是,提出“空间理性”和“区域人”的概念,将高技术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有限流动纳入“空间理性”的范畴,从而模拟出区域间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引入“政策限制系数”概念,将政府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限制也纳入模型框架,从而模拟出区域内低技术劳动力工资的城乡差异。
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出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城市群的形成和政府户口管理制度放松的情况下,沿海与内地劳动力工资差异及产业集聚的变动情况。模型的结果与目前我国区域差异的现实相吻合:在产业集聚、劳动力工资、中间产品种类数、生产者服务和城市化率方面,沿海领先内地;对外贸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加大低技术劳动力工资的差异、促进制造业在沿海的集聚和推进城市化进程;减小区域间贸易成本,有助于减小沿海与内地低技术劳动力工资的差距、减弱制造业向沿海集聚的趋势;减弱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有助于拉大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减小城乡差距、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群的形成,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在沿海的集聚、加大高技术劳动力工资的差异、拉大城乡差距。
总体来看,基于劳动力流动的新经济地理学区域差异模型,对于中国区域差异的走向具有比较好的解释能力,虽然经过了10年的时间,模型当时推演的结果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过,中国区域差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同题,模型能够对现实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并不能说明模型的基础和设计不存在缺陷。中国的区域差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融合主要因素、正确判断中国区域差异的机理等,才能真正对现实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新经济地理学自诞生至今,已经经历了20多年,融合了各种要素、改变了各种生产函数、丰富了多种多样的地理结构,试图不断地接近现实。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应当理解为“象征性”解释,即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的可能性给出具有理性的解释,而不应用于预测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趋势。区域间的壁垒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在具体运行中的隐形壁垒,同理,劳动力流动不仅有经济因素的影响,还有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交通成本即可体现为几种运输方式所构成的综合成本,更宽泛地说,也包括区域间的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中国政府在区域转移支付中发挥重要作用,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区域战略层出不穷,户籍制度改革面临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是区域差异的政策因素。因此,模型是在现实抽象能力的基础上对现实最好的描述,但并不是现实,致力于模型研究,是希望通过模型推演,更为理性地增强对现实的洞察力。
周洛华在其《金融的哲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中写道:“在印度人的世界观里,古代印度版图由一头大象背着,这头大象又站在一个乌龟的背上,你可千万别开口问‘那乌龟站在哪里’这样的话,否则,你只会把你的印度朋友置入窘境。”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总以为你能够解释现实,但却恰恰又新制造了“乌龟”这样解释不了的东西。进行科学研究和模型推演,是在一定假设条件和技术条件下,对某些经济现象进行某种解释或再现,借以揭示其中所隐含的某些规律。模型不可能完全再现现实,但通过模型推演,人类总在了解社会的路上知道得更多。总体而言,模型推演有意义,模型推荐结果别全信,因为模型结果不在于是否正确,而在于其为我们揭示了不曾直接看到的现实。
(作者系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