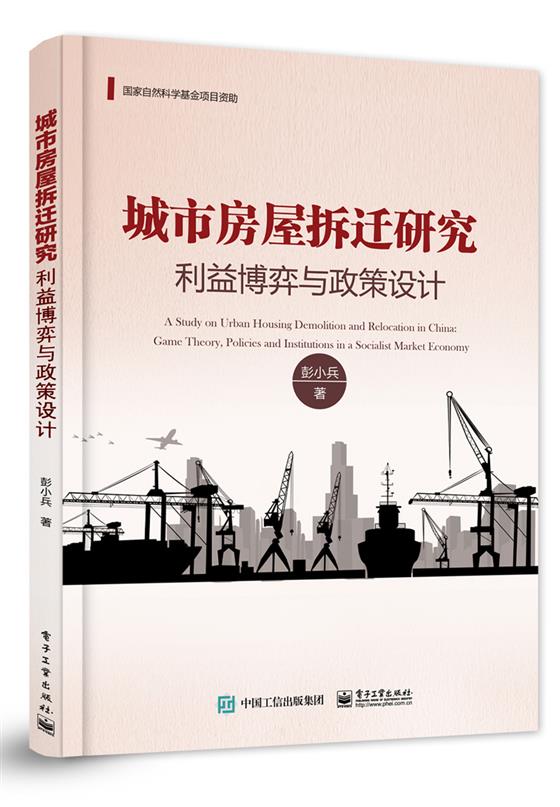城市拆迁中利益对立的阶级分析视野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社会矛盾及社会冲突,除了利益纠纷、利益对立的内在机理外,也可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国家角色有关。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渐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对英国早期“圈地运动”进行强烈批判的阶级观点,突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利益对立的结构性基础。按照阶级视野的观点,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主要是试图掠夺生产资料(土地)的资本方与正在失去生产资料(土地)的群体不对等关系的体现。因此,理解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社会冲突问题,以及城市房屋拆迁矛盾冲突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分析:没有土地或不能保障自己的土地的阶级群体的诞生与抗争;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关系的改变与再造;结构性格局中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实质性变革。
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由于土地国有,房屋只是土地的附着物,随土地的存在而存在,随土地的消失而消失;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追求即意味着,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之间展开激烈竞争,资本竞争的内在规律就像一种外在强制性的力量,趋势资本去不断掠夺生产资料,不断地囤积更多的土地。因此,理论上,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任何居民都是潜在的被拆迁人(注:比如近期温州、深圳等地的“房产70年到期续期问题”),即就栖息地、住房而言,这些潜在的被拆迁人实际上没有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实际上是无产者。
虽然马克思对资本贪婪本性的描述是基于18世纪英国乡村圈地运动和城市工场的生产,但在21世纪初的中国,在房地产行业人们发现了惊人的相似。虽然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兴起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然而这近20年却是一个财富迅速积累、极度膨胀和加剧分化的时期,地产业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聚宝盆,以至于多年来中国首富或富豪排行榜都集聚在房地产开发领域,“土豪”一词较多地用来形容地产商。但与地产资本一夜暴富的同时,是广大城市居民房屋、乡村耕地毫无保障可言的境地。在地产富豪老板们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是“强拆”、是“暴力拆迁”、是“血腥拆迁”、是“房奴”、是“蜗居”等等诸多刺激人们神经的字眼和社会现实。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城市拆迁和房地产行业的充分发展,确立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对立性的阶级结构。然而,在土地财政的追逐和城市发展的旗帜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房屋拆迁体制,掩盖了这种马克思笔下的这种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使得人们尤其是被拆迁人难以认清真正的老板——权贵资本。一方面,人们对城市改造的渴想以及彪悍的“维稳”机器,压抑、缓解和转化了城市房屋拆迁场域中的矛盾和冲突;可另一方面,由于它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阶级结构中内在的利益对立问题。因此,所谓的“维稳”机制,实际上从第一天开始就将社会矛盾和冲突暂时的拖延、进一步的积累、直至最后的爆发。以至于,在这种利益背景下所催生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体系,将资本圈地、资本对土地的掠夺程度推到极致,常常突破道德、法律和伦理的界限:譬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的某些条款甚至直接与宪法或物权法的法律精神相悖,导致在一些个案中,被拆迁人被推到了无法忍受的绝地,激起了反击与抗争。总之,城市房屋拆迁中的互动博弈,看似最简单的经济斗争(拆迁补偿),但却让资本与“无产者”之间内在对立、隐蔽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多年时间里,社会主义的建立(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抹去了人们的阶级意识。然而,最近20年来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使得人们的阶层意识又重新恢复了起来,某称程度、某种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在淡出人们的视野、经历了较为短暂的潜伏后,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且这种社会分野、阶层对抗、话语争夺的阶级分裂在网络新媒体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可是,基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特殊性,被拆迁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更具有它的复杂性,具有零碎、模糊、多变的特征,容易遭遇基层力量的稀释和扼杀。我们看到,被拆迁人的冲突与反抗仅仅是对基层政府的不满与怨恨,并随着基层政府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而变化,而极少直接对准资本,更非针对中央。在反抗强拆一些个案中,被拆迁当事人悬挂国旗,手捧宪法,播放国歌,企望于上级政府乃至中央的干预,幻想着资本及基层政府的让步或更可观的补偿。然而,资本的逐利本性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从某种意义上也地方政府的逐利本性)总是将城市拆迁推入到一个无法化解矛盾的境地。被拆迁人以及同情被强拆的人的其他社会群体,将来自多年来多方面的积怨与不满一点一点地累加,最终到某个特殊的关头(导火索),爆发为群体行动,震动社会和中央。这是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冲突与矛盾积蓄并发的阶级分析视野。
还有一个未触及的问题是,城市房屋拆迁领域(乃至其它群体性社会事件),被拆迁人的抗争究竟是阶级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呢?如果被拆迁人仅仅是为了捞取更多的拆迁补偿,那么可以把这种利益抗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斗争,这易于理解,很多城市房屋拆迁冲突后也的的确确最终总是通过钱来摆平了,也确实反映了这种抗争性质。至少从目前来看,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矛盾、纠纷、冲突乃至某些集体行动,基本上是围绕拆迁补偿而引发的经济领域的斗争,而且是针对利益受损的防御性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拆迁矛盾纠纷似乎都可以将它们称之为经济斗争。然而,如果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会漏掉很多关键信息。实际上,特别是最近十多年以来,在围绕城市房屋拆迁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中,我们也发现了抗拆集体行动背后的不断政治化的影子:其一,哪怕是最简单的利益纠纷及拆迁矛盾,都涉及到将单个被拆迁人团结起来进行集体抗争的复杂过程;其二,被拆迁人的反抗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基层政权发生关系,人们的每一次请愿,不管与政府有没有关系,我们总是看到要求政府的直接介入,他们要么直接求助于政府并与基层政府交锋,要么是援引宪法和法律来对抗资本,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势必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其三,人们还学会了要挟与利用,即不管遇到什么事,哪怕是人们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错误,哪怕完全与政府无关,也会转移责任,归咎于政府,产生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现象蔓延,因为长期以来,政府主导一切,政府的触角几乎伸入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因此人们无论有什么事都会首先想到政府,人们几乎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找政府,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其四,在网络自媒体上,无论出现任何一个集体事件或个案事件,总有人会借机发难,将纯粹经济问题、民间问题政治化。于是,我们总可以看到,包括城市拆迁矛盾冲突在内的几乎每一件事件,总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将政府、将国家、将公共权力官员卷入其中。城市房屋拆迁矛盾、纠纷与冲突的政治性特征也非常明显。这就意味着,考察城市房屋拆迁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利益冲突和情绪对立,不能忽视国家的重要角色。
进一步地,布洛威(Michael Burawoy,1985)提醒我们注意国家为规范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而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与治理手段。转化到城市房屋拆迁研究上,对土地的控制与抗争的探究,不但需要我们去了解城市房屋拆迁的微观运作,更需要我们去了解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建设中的中国,其国家性质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复杂得多,因为社会主义中国要承载着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同时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导航者,这使得中国的国家角色充满了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在对面频繁的社会冲突或资本与劳动群体的冲突时,国家必须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保护者形象出现,而另一方面,在实际拆迁纠纷、冲突处理时,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以及地方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关联,使得政府又会漠视被拆迁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以至于无论是公共利益拆迁还是商业利益拆迁都常常出现基层政府职能部门亲自带队参与强拆等事件,显示出了地方政府阶级属性亲资本的一面,中央许多的政策、国家的许多法规被流于形式,或被资本或地方政府架空。这就是“诺斯悖论”。
国家角色的内在紧张,使得城市房屋拆迁矛盾冲突的政治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并显示出了激进化倾向。具体言之,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行政执法部门在拆迁冲突中的表现,削弱了人们对于政府公信力、对于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信心,转而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依赖自身的力量,突出表现在“越级上访”、“上京信访”,即很多有过求助地方基层政府经历的人,当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就越级到上一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上访,或者选择在法律、行政渠道之外选择“闹事”的方式采取更激进的集体或个体行动,以破坏社会秩序的方式来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本来,在法治国家,法律渠道和集会渠道是用来调和劳资矛盾、规避阶级冲突的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党中央和国务院也比以往任何时候强调“依法治国”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决心(突出表现在2014年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问题是,权贵资本的普遍性以及地方政府的亲资本立场和做法,使得地方法律、行政渠道及救济机制形同摆设,结果自然会将被拆迁人群体(或社会矛盾冲突、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其他社会群体)推向冲击政府、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群体暴力性甚至带有某种阶级抗争意味的轨道上去。这不能不引起重视。
套用怀特的研究(Wright,2000),城市拆迁矛盾冲突和集体抗争的力量来自于“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和“结构力量”(structural power)。“结社力量”是指人们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基础,但中国缺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成熟的制度化抗争渠道,也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支持;“结构力量”是指人们在经济系统的位置,但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会起来反抗、“闹事”的被拆迁人通常是社会弱势阶层,他们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处于弱势的位置,城市拆迁补偿的议价能力非常低下。也正因为如此,城市房屋拆迁经常被突破底线,矛盾冲突的力量也就常常积累。如此,一旦“稳定”的临界规模被积蓄的力量突破,就会使得拆迁抗争的破坏力十分强大。资本的掠夺、共同的利益,加上生活中日积月累的其他不满与怨愤,使得集体的联合行动就成为了可能。
当然,一些传统文化,如“难得糊涂”、“忍”、“明哲保身”、“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以及城市社区居民宗族力量的缺失、农村社区居民宗族影响力的瓦解、制度性组织基础的缺乏,使得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领域的抗争呈现出个体性、自发性、分散性和野猫式的特征,大规模集体行动虽时有报道但毕竟不是主流,参与人数也不多。不过,城市房屋拆迁冲突往往是通过“闹”、采取极端化(如自焚、杀人)和充满暴力的手段来展现,往往一个或几个家庭因此就支离破碎,充满着人生悲剧,这种冲突方式及其产生的后果、这种家庭悲剧的其他潜在负面影响,对国家、对社会、对社区的破坏力也是十分巨大的,绝不能忽视。
(摘自《城市房屋拆迁研究:利益博弈与政策设计》(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