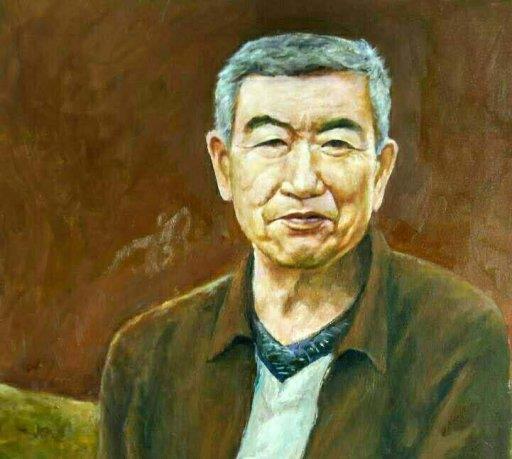
图片/冯山云画
京腔京韵亦润物(纪实散文)之一
作者:张瑞生
有人说陕北当代最大的两次次开放是,中央红军到陕北和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三十年代,那些来自南方的中央高层为夺取政权需要,拉紧了群众和党的血肉联系,培养了一大批陕北本地的文臣武将,有的则成为后来共和国大厦的支柱;那么六七十年代北京知青的到来则是缩短了偏远山区和大都市之间的文明差异,让普通山区农民在精神领域里受到洗涤。前者因为时间久远,逐步停留在历史资料之中,而后者则仍然活跃在上了年纪人的笑谈之间。
我家住在马家河公社,当时并没有北京知青,只来些西安莲湖区几十个下放干部以及刚从大中专院校毕业的青年学生。知青在一九六八年革委会刚成立不久就来到我县县城北部的几个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公社。我也和他们一样,也是由红卫兵小将突然间变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象。我们被称为回乡知青的农民子女,必须要接受和他们一样的诸多限制条件,但绝不能享受他们的许多升学招工优惠政策。
因为当时消息闭塞,对刚来的北京知青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我在村里劳动时,只是听到传言说,这些毛主席的小客人,不仅浪费和糟蹋粮食,有的爱打架,还有的小偷小摸,甚至说有的同学还批斗稍微有问题的农民等等一系列负面消息。后来我经过打问,了解到这些事情确实存在,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好。大约在六九年夏天,县上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也去参加。在大会交流时,我发现这些北京来的同学,上台发言非常积极。而本地学生比较胆小,更不善于处处突出自己。据后来听别人讲,几个崭露头角、口若悬河的,没过多长时间都去部队参军了。其原因是这些人都有背景,像空中飞人一样,在台上信誓旦旦,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话音还未消去,早已远走高飞。又一年(可能是七零年)冬天,县上又召开体育运动会。我们公社教育专干王锡光让我和公社医院郭辉(从陕西省卫校毕业,户县人)去参加乒乓球比赛。我一再推辞说,自己水平低害怕给公社丢人。但因为王是我城关小学老师,加上我在马家河学校教民校,于公于私,只好勉为其难。这次运动会主要是北京知青为主。他们无论哪方面都远远高出当地青年。尤其是足球,,连我们这些高中学生过去都没有见过这项运动,在县城叫“井滩”一个平地上,展开了第一次比赛。就其参加人员组成来说,县上这次运动会可以称作为北京知青运动会。通过这两次与他们接触,这次让我大开眼见,充分看到北京知青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非常优秀的。这是我对北京知青直观而表面认识。随着转正成为公办教师后,自己觉得底气足了,而北京知青也相继进入各个单位,于是多层次交往便开始了。
刚开始到张家河教学时,因为离县城较远,虽然这里有分配来的八年制大学邱贵兴两口以及后来成为省人行行长的苑羽鸣,这些以后能叫响的大人物。但可能是出于照顾原因,那里并没有几个北京知青干部。当时这里修了个大水库,大家经常去游泳。只有粮站的北京知青叫安建华,速度最快,能游到一百多米。我想起过去运动会便开玩笑说,啥事都让你们占全了。此人最大特点是对农民态度好,遇到农民交公购粮,和言细语,从不发火。但对机关干部要想违反规定多买点细粮,则是寸步不让,尤其那时教师地位低,学校买粮从不给予任何关照。供销社有位女售货员叫张卫民,眼神里好像经常有点瞧不起农民的样子。一次坐手扶拖拉机,突然刮起大风,天气变冷,开拖拉机的农民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让她披上。可她大概是嫌人家衣服脏而不想穿。后来大概是冷的不行便又穿了上去。我笑着用讽刺的口吻说,驴渴得不行了,会自己奔向井子去的。她当时没听明白我的意思,一再追问是啥意思。我便说你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此话一出我有点后悔,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这几个岗位的人在当时最吃香。可最后结果与我的想法,恰恰相反。张卫民后来并没有计较,反而主动问我需要啥东西。当时我的孩子没奶吃,经常要买白糖,这在当时是紧俏商品,过去数次求她都无济于事。打这以后,她再也没有为难我。后来她调到县城百货公司不久便离开延川。
后来随着工作调动,与北京知青交往进一步密切。七三年下半年,我又回到马家河中学。当时公社、学校、医院、供销社、粮站所有机关干部总共才二十人左右,北京知青就有五个。最早熟习的是粮站的杨永利。他没事时会经常找我闲聊,相互交换文革时期的一些经历。他还给我唱当时北京文革中两派群众相互斗争时编写的几首歌曲。其中一首歌词是:离别了挚友,来到这间牢房,已经七十五天,看到的只是铁门和铁窗。不见了战友,不见了爹娘,只有那泪水仇恨满胸膛·······。他是在给我讲故事,而我却是看到歌词内容不错,想提高一下自己文字水平。这年冬天他回北京,第二年来时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捎带给我买了件衫子。当时缝纫机不太普及,大部分干部都是穿自己家人手工缝制衣服。北京买来的衣服很合体,但价格高达九块钱。这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因为我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八元。他可能看出我的心思说,你小子别不识好歹,布票还是我家的。当时我不缺少布票,可各省市间布票粮票不能通用。我穿上后说,钱得慢慢给你。这是我第一次穿买下的成衣,穿上之后大家都赞叹不绝。当然我知道他的这份情谊,不久便从别人处借来钱还给了他。到夏天时,他给我说,知道你很困难,他们粮站有些麻袋要洗干净,一条五分钱。我很为难地说,我已经是教导主任,这样做让人家知道了,要受批判的。杨永利说,礼拜天学生老师都回去了,你别回去。在金钱的诱惑下,我把麻袋背到学校对面的小河里,找了没有人能看见的地方,洗后晒干。就这样偷偷摸摸干了好几回,一年内洗了一百多条,挣了五六元钱。现在看起来几乎不值一提,可当时对我来说,那真是雪中送碳。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时粮站供应面粉有一定限制。虽然他们领导是我远方堂哥,但每当我提出有所照顾时,这位小官常要摆出公事公办的样子。杨永利趁他不在时,跑来告诉我说,你村里的人不在了,我给你全买成细粮。这样,大家都认为我和他关系要好。在收购夏粮时,我村因交不进去儿找我说情。这时杨永利大发雷霆说,以后不要再说了,粮食晒不干,倒进库房,坏了怎么办?可见他在重要问题上,原则性还是很强的。最让我感动的不是这些。最近听说杨永利为一位当时的临时工后又被辞退的老年人帮了大忙。前几年他在北京得知,过去在国家单位被辞退的临时工,可以享受一定养老保险的消息后,专门来到马家河,帮助他予以办理,问题得到解决后,他于去年又自己开车看望了这位七十多岁的同事。此事在当地传为佳话,令我无比感动。相比之下,那些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当地人,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当时在马家河还有一位供销社职工叫李学明。他看不惯领导某些做法便会当面顶撞。可他对于朋友还是非常热心。他在单位是收购员,记得有一次,他们领导不同意在一次端午节时杀猪供给单位和农民。可他就是不服从,硬是收购了一头猪而杀掉。气得领导没有办法,经常在广众之处说他的坏话。这样,两人矛盾越来越尖锐,闹得不可开交。一次我以兄长身份劝他,以后不要没事找事,顶撞领导。李学明便把领导在上级部门和周围说过他的坏话,详细学说了一遍后后说,你是领导,当面批评我两句都可以,但不能没有事实根据就在那里乱说,我也是有意气他,看他有多大本事。后来我了解到,当时生猪属于计划商品,每年农民必须按照上级指令交售生猪,价格也是国家按照肥瘦而定。领导害怕将来不能超额完成县上下达任务,影响自己政绩。就这样,李学明给大家谋了福利,赢得不少人的好感,而那个领导却因四处说下属坏话,变得更加孤立。当然我不仅为家人买回去猪肉,让父母高兴,同时我由此吸取了教训:作为领导,可以在办公室狠狠批评下属,但千万不要四处说他们的坏话。这一教训使我以后工作中受益不浅,无论在哪个单位,和大部分同事关系较好,虽然在工作中可能产生摩擦,但基本上没有十分对立情绪。
当时在马家河公社有三位女知青干部。邓桂芝和刘淑珍分别为团干和妇干,蔡玉珠则是公社书记。虽然因工作关系接触不多,但和我关系还是不错。邓桂芝、刘淑珍两个经常给我讲在北京上学时,每遇到有重大活动时,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手持鲜花,唱歌跳舞。听到她们诉说,我有时便会情不自禁产生诸多感慨:我们上自习还点着油灯,不知电灯楼房是什么样子时,人家已经参加欢迎外国元首活动了。实事求是讲她两人在工作中并未做出什么特别贡献,但却在改变当地妇女在服饰和卫生方面,产生了不小影响。当时由于物资匮乏和观念落后,乡下人大都不会炒菜,通常做法是把所有的菜烩在一起,用现在通行的叫法,就是大烩菜。她们两人在下乡时,经常给妇女将北京的轶闻趣事,教育当地农村妇女如何讲究卫生,特别是生理卫生。受传统封建观念约束,过去当地农村女人几乎一辈子不洗澡。刘淑珍在乡下时常动员在河边生活的妇女,在夏天中午劳动后,和他们在偏避处一起洗澡。起初有些人还害臊,觉得女人赤身裸体,有伤风化。但慢慢地人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不要小看这些琐事,妇女包括整个基层的解放都是从小事开始。
由于马家河公社好几个村子都在秀延河边。每当夏季发大水时,河里会有许多柴草。许多人借机捞上来作为做饭取暖燃料。这时男人们会脱光衣服,全身一丝不挂站在河边。不知是何原因,当时多数人不穿裤头,甚至干部中也是如此。大部分农民的被褥常常会留下洗不掉的图案,有人开玩笑说是“绘地图”。刘淑珍、邓桂芝俩人每到一处,都给妇女讲解裤头缝制技术和好处。就这样时间不长,这个服饰就全面推行开来,河边捞柴草的人不再赤身裸体。一些女人,特别是干部家属也敢去河边和男人站在一起捞柴草,以解决燃料匮乏问题。老乡海波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北京时,邓桂芝给他帮过不少忙。可见这些知青仍然把延川人当做自己的亲人。
现在媒体经常有年轻人当官,舆论就会一边倒认为,此人一定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可是蔡玉珠这位北京女知青,当年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马家河公社书记时,也就是二十四五岁,还没有结婚。群众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她是有啥特殊背景,最大疑惑是觉得提得这么快,能不能胜任。她原来在文安驿插队,一直表现的很好。听说她要来时,机关干部和农民都私下说,她可能不懂农村工作,上的太硬,让人会受不了。有人甚至怀疑毛主席当时提出的老中青三结合干部方针是不是错了。
蔡玉珠来到公社担任书记后,给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显得非常硬气。但是任何一种东西做过了头,便会适得其反。一次全体公社干部在一个村子里召开现场会,还要参加劳动,蔡玉珠把裤子挽到膝盖上,汗流浃背。干部都是每顿饭半斤粮,蔬菜也不多,公社炊事员觉得书记太苦了,一定饿得不行,便利用自己关系在偷偷给了她一块玉米面做的团子。可是蔡玉珠不但不领情,反而立马在干部会上对这位炊事员进行了公开批判。作为一把手,严格要求自己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对待下属,方法显然过于简单粗暴。更为硬气的是,一年冬天公社提出要早五点晚七点晚上赶到十二点,进行农田基建大会战,要开肠破肚夺取大丰收,实现三变五翻奋斗目标。这些措施劳动强度太大,加上冬天滴水成冰,自然引起农民不满,推行起来阻力较大。一次蔡玉珠早上起床从公社走到十华里外一个村子,发现农民还未起床,便不由分说,一脚踢开一家门,这家人吓得浑身发抖,赤身裸体裹着被子不知如何是好。更为硬气的是,她把粮站职工杨永利在晚上带到一个农村去批判。杨永利也是北京知青,向来不太尊敬领导。据说在回公社的路上两人发生争吵时,杨永利曾恐吓蔡玉珠要做出非礼行为。我听到单位干部私下传言后,曾问过杨永利,告诫不可鲁莽从事,但他不置可否。和那个时代的干部一样,蔡玉珠从不接受任何人礼物,下乡吃派饭,无论饭菜质量如何,都按规定付给群众粮票和伙食费。一些善良纯朴乡民不收时,她会吊着脸把人家美美收拾一起,弄得人家反而下部了台。后来我到公社工作后经常下乡,知道农民心地善良,有些人家觉得没有啥好饭招待干部,往往心存愧疚。时间一长人熟悉了,农民一般不会收伙食费,如果你再板起面孔,显出公事公办的样子,人家会以为你瞧不起他 ,反而使关系产生隔阂,不利于真实全面了解实际情况。
蔡玉珠还有更硬气的举动,现在想起来有时觉得好笑。冯山云给我讲了件事,让人忍俊不止。一是一家办丧事,孝子跪在灵柩前哭啼。当地风俗是孝帽上有个布帘,哭灵时用布帘遮挡住面部。蔡玉珠不顾人家悲伤,上去揭开布帘,发现其中一人没有眼泪,便对这家人说,没有眼泪,哭啥里。其实丧葬方面有一套固定程序,约定俗成,谁要违背,难免会遭人非议。此事发生不久,一位德高望重的村党支部书记父亲去世,蔡玉珠反复交代不能请阴阳先生、不能披麻戴孝、不能待客,否则要进行批判。这位书记说,别的还好办,帮助我打墓抬棺材的总不能不给人家管饭吧。人家给我帮忙耽误劳动没有了工分,连饭都不给吃,这怎能说得过去?
蔡玉珠更为硬气的表现在劳动方面。她每得到一个村子,即使是大冬天,也会脱下棉袄,劳动起来比农民还卖力,经常是汗流浃背。在一个村子的改河造地劳动时,她双脚踩进冰冷刺骨的泥浆里,比普通社员还要肯下力气。这些都给当地人留下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这些超过常人生理极限艰苦奋斗精神,使大多数善良的农民,原谅了她在工作中因执行极左路线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冯山云最近给我讲了一位叫高国兵(现已经是部队师职干部)参军的经过。当年他要报名参军,心想农民子弟,无依无靠,找公社书记总得给个啥东西吧。于是他便从家里带了一把韭菜。谁知蔡玉珠听罢来意后,脸色大变,把他带来的韭菜扔到门外去,还说你这样的思想根本不能去参军。该同志直到蔡玉珠离开后才报名参军。现在反观此事,蔡玉珠防微杜渐,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确实值得赞扬称道,但是在处理问题方法上显然有些失当。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蔡玉珠偏颇于硬气,有时会适得其反。那时农民生活已经非常枯焦,可是各类负担有增无减。最要命的是,有一年蔡玉珠要大家多交爱国粮。本来国家强制性低于市场价格好几倍征收农民粮食,已经是一笔沉重负担。再让多交粮食显然已经超出他们心理底线和负担极限,大队干部几乎是一致反对。海波在《回望来路笑成痴》一书中有详实记述。冯山云当时担任支部书记,因不愿多交粮而受到批判后,愤怒地把各类奖状从墙上揭下,撕碎后踩在上面,表示以后再不当这个先进了。其实蔡玉珠当时也很为难,上面的政策她要坚决贯彻,加上自己又是县革委会副主任,自然要走在其他公社前面。这样无疑给自己树立了对立面,就连一些德高望重的基层大队书记,也不满意其征购过头粮的做法。
我当时在学校教学,其实和蔡玉珠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但有几件事情回想起来,觉得她这个人心底还是不错的。有一次她在大队书记会后,向大家介绍北京的一些情况后,和公社主任赵长青开玩笑说,当时我们决定来延川插队时,你来接我们时说,延川山清水秀,红枣皮薄肉多核小。没想到来后看见这里十分荒凉,山上光秃秃的。说着大家笑了起来。另一件事是,公社有两位副主任因工作方法不一而相互闹矛盾。蔡玉珠说经过协调仍然无济于事,表示自己不会偏向谁。其中一位虽然文化程度比较低,但是非常熟悉农村工作,在工作中时常与她发生争执。可见蔡玉珠基本上还能抛开自己情感因素,处理问题比较客观公正。我自己的一件事,也可印证蔡玉珠心底不坏。我在张家河教学时,学校支部曾三次向公社党委提交我的入党申请,但每次都是说要继续考验。到马家河后,学校又把我报到公社。我当时从过去经验出发,觉得不可能批准,一是只有半年时间,组织还没有好好考验自己,更重要的是,我和杨永利关系好,蔡玉珠知道后,一定会计较的。没想到不久,公社党委会便顺利通过后,上报县委组织部,使我成为一名党员。那时入党是件很难的事,此事的解决,着实让我高兴了好长时间。
蔡玉珠在马家河时间不长,便调到延安地区知青办担任副主任,临走时单位干部与她合影留念。农村中对她的评价是:她确实是把力出扎了,扑下身子干工作,对于工作中出现失误而伤害了一些人,大家没人计较,都说当时的社会坏境就是那样。有人为他编写了一幅对联:一颗红心,单肩挑重担,精力耗尽而难上云端;两袖清风,双脚满泥土,汗水洒乡间,青春化灰却易植民心。
后来我在禹居公社时,接触到的北京知青,大部分还是留在农村未吃皇粮最后守望者,不久他们随着各种渠道,离开农村。我曾写过风《卷残云》一文,这里不再赘述。
一九七七年我来到城关公社和广播站后,发现县城各单位几乎都有北京知青。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单位业务骨干,有的已经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队伍随着这些新鲜血液的增加,对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服饰、饮食、风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经济条件好的当地人想方设法托熟悉的北京知青回京买比较时髦的衣服。有的学着做菜。尤其是过去当地人不敢公开谈恋爱,男女上街都不敢并肩而行,否则便会有风言风语。这种封建陋习随着知青增多,有了很大改变。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知青回京后带来许多中央高层内幕,但是被称为小道消息。而这些所谓被追查的小道消息,在后来高层政权更替后都得到证实。总之,北京知青在开化当地人思想进化方面,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为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北京知青思维活跃,自然在工作上常常令我折服。我刚到城关公社不久,由于七七年延安遭遇大洪灾,秋粮损失严重。中央决定给我县空投菜籽。当时绝大部分人不仅没有坐过飞机,除空中外,地面上谁也没见过。因为这是本县第一次有飞机降落,如果弄不好影响飞机降落,还会出安全大事故。那天人山人海,大家聚集在体育场,等待着看飞机降落。城关派出所只来了一位叫张学军的警察维持秩序。那时人们比较老实,严格按照要求站在规定区域内。也有几个人因为是县上头面人物,当时还没把这位警察放在眼里。我当时想,其中某人为县计委主任,他要是不服从安排,别人也会乘机跑进去。张学军在安排好其他人后,对这位领导说,张主任,请您帮助我一下,您是领导德高望重,您带个头,给大家做个榜样,我就好维持秩序了。经过他这么一说,这几位头面人物再也不好意思违反规定。这么一个难题,被张学军和风细雨方式解决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毛主席说过,任务是过河,方法是桥和船的问题。可见不同的方法会带来不同效果。这一事给我以后担任领导后,在注意方式方法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古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和原来宣传部干事吴美华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至今让我对她难以忘怀。粉碎四人帮后,县上组织各单位干部每天早上在影剧院学习政治经济学。以前学的都是阶级斗争理论。宣传部在给大家讲解这些陌生的学问时,有个女北京知青叫吴美华,初中学生,应该比我低好几级。可她讲起来,条理清晰,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让人容易理解。可以这样说,她是我学习经济学的老师。碰巧的是,到八三年,我参加新闻系统考试时,要考政治经济学,由于我之前有一定基础,复习起来比较轻松,最后还考出好成绩。恢复高考后,吴美华这个初中未毕业的知青,竟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据说被评为教授,还担任了该校宣传部长,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宣传部还有一个叫张兴祥考入西北大学,还在农村劳动的丁爱笛考进上海机械学院,在张家河担任公社书记的陶海粟则考上北京大学。而本地回乡知青,初中生没有一人考进大学,高中毕业的,除申安秦考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其余都是大专居多。由此可见北京知青志向和学识水平高出当地知青许多。
随着对他们了解增多,发现这些北京知青中大部分人,并没有城市人鄙视农民的恶习。城关供销社有两位女知青苏立琴、孙维梅,她们对待农民非常和气可亲。在收购农民货物是从不压级压价,尽量给提供方便,颇受大家好评。对我影响深刻的还有粮站两位女知青杨桂春、王翠玉。七七年,因上年遭灾,因而国家给城关公社各村救济粮高达二十二万斤。分发粮食是件很麻烦的事情。首先是公社根据各村情况,将指标下达各大队。各大队再分配到各家。我当时为了减少自己工作量,便把复核任务交给了她两人。她们认真负责核对,保证每一个大队数字上不发生差错。同时还要将这些粮食再以户为单位,逐笔开票。因为除我们外,还有周围几个公社,也在这里买救济粮,再加上县城各单位和居民正常口粮供应,几项加起来,这个工作量是相当大的。这两位女知青只要看到农民来买救济粮,即是推迟下班时间,也要保证农民来了就会买到,不让他们多跑一次路而耽误生产影响生活。她们常对我说,农民实在可怜,为买救济粮喝不上水,吃不上饭,买好后还要自己顶着烈日背回去。因位有工作关系接触,我和这两人逐渐熟悉起来。我到广播站自己做饭时,他们两常会对我有所照顾,尽量给我多买些细粮。这令许多人着实羡慕,有些人还通过我,走他们的后门呢。
北京知青中,还有一个叫关来英。她原来在县宣传队后调到城关小学。之前我和她并不熟悉,甚至没说过话。我到广播站后,想把自己的长子由乡下老家转入城关小学,以便将来进入县城中学。当时我离开教育界不久,该校有我许多同事同学。考试前一天,我领着儿子来到学校,想问一下有关考试情况。刚到学校院子里,碰到关来英。她主动问我有啥事。我告诉她孩子要考试,看看情况。她问学得怎么样。我说在村子里不错,可放到这里就不知道了。她蹲下身子顺手掏出一块糖给了我儿子,然后出了几道数学文字题考他会不会。乡下来的小学生开始显得紧张,大概是受到糖果鼓励诱惑,神情逐渐放松开来,没费多大劲 ,答对了了这几个数学题。关来英很有把握说,估计不会有啥问题,这娃学得不错。第二天考试结束后,我发现数学题除内容和数字不一样外,运算法则则是与昨天关来英测试的基本一致。后来我从同学那里打听到,数学题就是她出的。这时我才明白,她为啥敢肯定回答说我儿子能够考上。儿子在城关小学学习后又到县城、延安读中学,之后考入大学,便有一分不错的工作。儿子凭借自己实力顺利考入,但是对于关来英这份情谊,我一直珍藏在心。后来听说她去了张家口。除过他们宣传队某年在延川聚会,见过她一面外,在没有联系。
总之这些北京知青都是或大或小对我有过帮助和启发的,从他们身上,我汲取许多学养,逐步使自己为人处事和思想观念产生巨大飞跃。
(未完待续,海波建议网上文章不要太长,故将先写好的这部分发出来。其实该文也不短,以后另做新的部署)
张瑞生2014/4/11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