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修在西伯利亚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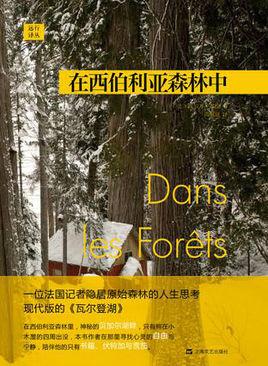
读法国探险家西尔万.泰松写作的现代版瓦尔登湖《在西伯利亚森林中》一书,作者描述了六个月隐居在贝加尔湖畔那段孤独而有意义的实验生活。他验证了:目的越少,生命就越有意义真理性。这里,离他最近的村庄在一百二十公里以外,这里没有邻居,只有偶尔的奇怪访客,从冬天到春季,他与暴雪和乌云相邻,他与山峦和寒冷相伴,他带了书籍、雪茄和伏特加,时间缩减为几个简单的行为:面朝湖泊和森林,注视着日子流逝,砍柴,钓鱼,做饭,大量阅读,在山间行走,在窗前喝伏特加,自创了一种逃脱城市朴素而简单的美好生活。
在他看来,孤独是最难保护的东西。世界因我们的乏味而灰暗。真正的爱就是承认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事物价值。他驶向荒野,既不带记忆,也不觉愤恨。将纯洁的时间变成一座宝藏。使时光的流逝比旅程行走更加纷乱。也让眼睛永远不会厌倦壮丽的景观。

当你对一个地方感到熟悉之时,这其实是死亡的开端。他逃避到西伯利亚森林中这九平方米的小木屋,最终成为他的静修所。他享受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不可缺的两种因素:孤独和辽阔。
为了获得内心自由的感觉,必须有充盈的空间与孤独,对时间的掌控,绝对的宁静、粗粝的生活,以及触手可及的自然美景。所以,他将自己的行为简单确定为以下方式:阅读、写作、捕鱼、登山、滑冰、林中散步……生存仅剩十五种活动。实用性、物质性的自治所取得的胜利似乎并不比精神智力的自治少一分高贵。

幸福就是对平静的羁绊。物与物之间存在着无从估计的联系。任何思想家都不敢说山楂的香气于星群无涉, 敢断言波浪在幼兽打梦中无足轻重。在物质丰富的时代,是过着满脑肠肥的生活,还是成为僧侣,在书本的低语间消瘦度日。作者的回答是:拒绝自己的时代,不惜一切代价来到森林,人们可以在内心的穹顶下获得安静。
亲近野物能令人返老还童。野性给人慰籍。我们这些工业动物根本理解不了自然原本的智慧就在这里。终归山林,任凭俗世自生自灭。盘中是捕来的鱼,杯中湖里打来的水,火炉里是自己砍的木柴,这便是一种幸福。这里有森林的忧郁,山洪的欢乐,沼泽的犹豫,山巅的严肃,蛮荒大地没有我们完全可以过得很好。

在作者看来,回归森林这种方式只能由少数人进行,隐修论是一种精英主义。隐士的朴素在于既不被外物,也不被自己的同类所困扰,摆脱自己对以往那些需求的习惯。他如五世纪埃及沙漠中隐士那般生活,静修无法预见的是他的思绪,只有它能打破时光一成不变的进程。为了给自己带来惊喜,必须梦想。为了正确地开始新的一天,先向太阳致敬,然后是湖泊,最后是在小木屋前的小雪松,每个晚上,月亮的明灯就挂在松树的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