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委瑞内拉与智利最具可比性。一、两国的共性是都是富资源国,委国富有石油资源,智利富有铜矿;二、两国的问题都是内生性,且都是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且二者一脉相传——都是因为大搞国有化、大搞社会主义、大搞福利主义。最具可比性,自然也就最具借鉴性。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委国之困
委内瑞拉正在陷入一场新经济困局。
据《纽约时报》8月16日报道,截至15日,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已高达32714%。
对此,委内瑞拉政府试图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发行一种新货币,起初是要划掉旧纸币上面值的“三个零”,并更换纸币颜色。
对此,市场和经济学界并不买账,现行货币“强势玻利瓦尔”仍在持续贬值。随后,该国决定再划掉“两个零”。
7月25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名为“主权玻利瓦尔(sovereign bolívar)”的新货币将从昨天(8.20)开始流通。他同时宣布,1主权玻利瓦尔将从原先计划的等于1000现行货币强势玻利瓦尔,改为等于100000强势玻利瓦尔。
马杜罗的这一计划会否成功,看看委国的货币发行史,就不由的让人替他捏一把汗。委内瑞拉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1498年哥伦布航行美洲时到此。1523年西班牙人建立第一个殖民地。1567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11年7月5日独立。1830年建立委内瑞拉联邦共和国,1864年改名委内瑞拉合众国,1999年12月改为现国名——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自其建国以来,该国所使用的货币一直被称为玻利瓦尔,直到2008年。该年1月1日,委内瑞拉实行了货币改革,作为货币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重新发行新货币——强势玻利瓦尔(bolívar fuerte),以取代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变的一文不值的玻利瓦尔。强势玻利瓦尔与玻利瓦尔的兑换比率是1:1000 。讽刺的是,“强势玻利瓦尔”并不强势,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处于持续贬值状态。以致于委国政府不得不再次祭出货币改革的大旗。
正如从“玻利瓦尔”到“强势玻利瓦尔”的表现来看,如果委国不想做根本之改革,而是单纯的改发另一种货币,那么“主权玻利瓦尔”的未来也就可相见了。
那么,何以解委国之困呢?怕是唯有“芝加哥男孩”了。
智利经验
委国与智利最具可比性。
一、两国的共性是都是富资源国,委国富有石油资源,智利富有铜矿;
二、两国的问题都是内生性,且都是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且二者一脉相传——都是因为大搞国有化、大搞社会主义、大搞福利主义。
1970年,智利总统大选,阿连德所在的社会党联合共产党和激进党,组成了“人民团结阵线”,联袂出击。在选举中阿连德斩获了36.2%的选票,而前总统、保守派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则获34.9%,政治色彩居于二者之间的基督教民主党所推举的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Radomiro Tomic)获27.8%。阿连德虽以微弱优势领先,可所获选票未达半数,按照智利当时的宪法规定,如果没有总统候选人获得过半票数,那么就需要由国会从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通常的做法是选择得票最高的候选人,然而也有例外。譬如1958年,国会就选择了在大选中获得31.6%选票的亚历山德里,而不是得票更多的阿连德。在经过各政党之间几轮的谈判磋商之后,智利国会最终还是选择了阿连德,条件是要他签署一个“宪法承诺条款”,保证尊重并遵守智利宪法,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能破坏宪法的任何条文。
综合熊彼特和马克斯.韦伯的论述,所谓的民主,就是在复杂的社会中,一种提供法定机会,可定期更换施政官员的政治体制,以及由居民中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对竞选政治职位者的选择来影响重大决定的一种社会机制。加塞特在谈到民主时亦指出,民主所关注的是,谁来行使公权力,其答案是全体公民。李普塞特则在此基础上将其条件进一步具化,他认为所谓的民主至少包含如下3个条件:
A、指明何种制度——政党、新闻自由等——是合法的一套政治准则或一组信条;
B、一套在职的政治领导人;
C、一套或多套获得承认争取当选的领导人。
于他看来,如果一种政治制度不具备一套容许和平“运转”权力的价值体系,民主就会成为无秩序的。
参照以上定义和具体的条件,那么,我们可以说的是,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之前的智利,无一不符合民主政治体制的标准。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社会经济均陷入了严重的混乱(这一点也为巴罗研究所得的结论——如果已经获得了适度的自由,更多的民主就会遏止增长——提供了实证支持)。造成这种局面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阿连德这个对穷人满含同情心的左翼领袖,不顾国情、不顾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不顾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做的——生产关系总是同当时他们的经济力量所具有的那个生产能力发展阶段相适合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所以,是生产制度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纯粹的精神生活的过程。他们的存在不仅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相反地,人的意识本身则是依赖于它们的存在——的教诲,而强力推进他极富共产主义特色的社会经济改革。
就职后,阿连德开始大规模的推行被他称之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内容包括进行大型工业(铜矿、银行等)的国有化,彻底改造医疗卫生系统,改革教育系统,给儿童提供免费牛奶,深化前任总统弗雷的土地改革。由于当时智利宪法规定,同一人不得“连续”担任两届总统,每届任期为六年,这可以解释阿连德为什么要那么迫切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因为于他和当时的左翼而言,要想使他们的事业得到继承,他们不仅要在任期内很好地组织起这次社会经济的大改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务求获得成功。
阿连德政府的具体措施包括:开征“溢利税”,延期偿付外债、对国际贷款人和外国政府的债务不予偿还,提高工资、同时冻结物价。其政策的中心是土地改革,这一改革在前任总统弗雷执政时就已经进行了。弗雷政府没收了全国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易于接管的财产,而阿连德政府的目标是没收所有超过80公顷且有基本灌溉的土地。此外,阿连德希望通过实施国有化的企业或者公共工程项目为穷人们提供工作机会,以此来改善最贫穷国民的经济社会福利。
阿连德任期的第一年,在其经济部长奉行的扩张的货币政策的配合下,经济状况一度十分喜人。该年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达8.6%,工业增长更是达到罕见的12%。同时,通货膨胀率也从他上任前的34.9%降至22.1%,失业率也出现明显的回落,至3.8%。
然而,这种无视经济发展规律、肆意破坏私有产权和经济自由的行为,很快就得到了规律的回击。随后的一年,即1972年,智利的通货膨胀开始急剧恶化,从前一年的22.1%迅速的冲高至140%,且表现的无法控制。与此同时,出口下降24%,进口上升26%。面对这种局面,政府的应对之策不是从提高企业和商人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供给和控制货币增长着手,而是采取一种古罗马帝国时期迪奥克莱汀大帝的——冻结物价——这样一种愚蠢的办法。这一政策使得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面粉的价格飞涨,超市货架上也看不到这些基本货物了。此年8月,短短一个月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就从190埃斯库多上涨到421埃斯库多。虽然阿连德在1970年和1971年数次提高工人工资,但都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吞噬。智利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与工资上涨相匹配的改善。
恶性通货膨胀和商品短缺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这让民怨持续累积。1972年10月,阿连德上台后的第一波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终于爆发。大量的卡车司机和小商人,及一部分职业团体和学生组织走上了圣地亚哥的街头。这场大罢工持续了近一个月,这令本已受沉重打击的智利经济雪上加霜。好人阿连德为此担忧的心脏病都发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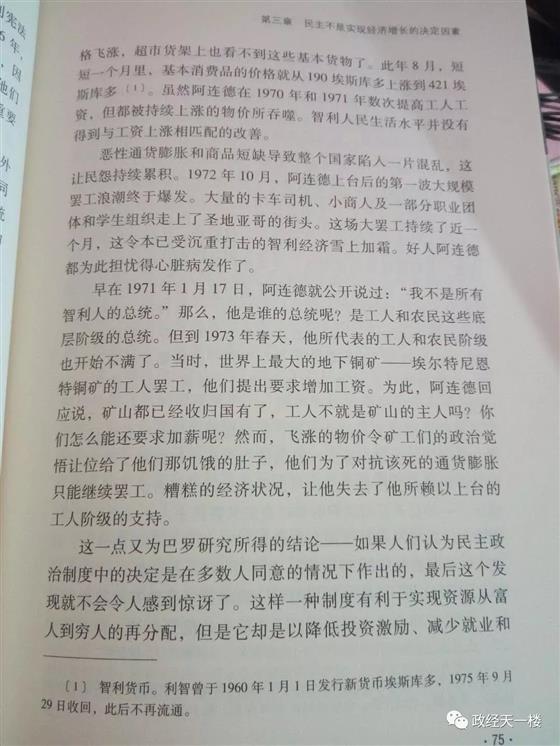
早在1971年1月17里,阿连德就公开说过“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那么,他是谁的总统呢,是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阶级的总统。但到1973年春天,他所代表的工人和农民阶级也开始不满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铜矿——埃尔特尼恩特铜矿的工人罢工,他们提出要求增加工资。为此,阿连德回应说,矿山都已经收归国有了,工人不就是矿山的主人吗?你们怎么能还要求加薪呢?然而,飞涨的物价令矿工们的政治觉悟让位给了他们那饥饿的肚子,他们为了对抗该死的通货膨胀只能继续罢工。糟糕的经济状况,让他失去了他所赖以上台的工人阶级的支持。
这一点又为巴罗研究所得的结论——如果人们认为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决定是在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做出的,最后这个发现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这样一种制度有利于实现资源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但是它却是以降低投资激励、减少就业和放缓经济增长为代价的——提供了佐证。
是的,如我们在前面所论的,好心肠并不总能结善果。纵然阿连德忧国忧民导致生病,但这无助于生产出更多的面包、无助于让通货膨胀稍微的下降......社会经济反倒更趋恶化。他那过于激进的政策,逼的像基督教民主党这样的中间党派,也不得不一步步右倾,直到昔日的这个非正式盟友与右翼的国家党结成联盟。自此,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矛盾陷入僵局。此外,最高法院亦公开抱怨政府执行土地法不力。
这种混乱的状态,给军人们提供了机会。阿连德一直对军队抱有幻想,基于历史经验,他坚信智利所拥有的数百年的民主传统,足以感化和约束军队,使其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坚守政治中立的立场。他一直认为“军队才是阻止或挫败任何政变的最有效的力量”。但事实却是,1973年9月11日清晨,出任智利陆军总司令还不到1个月的皮诺切特,与空军司令古斯塔夫.利等将军联袂发动政变,这些将军们命令军队开进首都圣地亚哥的市区,迅速占领了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并将民选总统阿连德杀死。
委国亦然。
今天要寻找委瑞内拉政治经济制度崩溃的蛛丝马迹,离不开对一个人的认识,这个人就是当年鼎鼎大名的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1954年7月28日-2013年3月5日)。
查韦斯是拉美的传奇人物。他发动过一次未遂兵变,经历过一次未遂政变,战胜过一次罢免性全民公投,连续赢得四次总统大选,还成功推动允许无限期连任的修宪公决。他留给委内瑞拉的最大遗产是以“玻利瓦尔革命”和“21世纪社会主义”为口号的查韦斯主义模式。
1999年2月就任总统后,他便开始推行“玻利瓦尔革命”。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年)是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5国的解放者,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英雄和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主张民族平等和废除奴隶制,并倡导美洲团结联合的一体化运动。查韦斯自诩西蒙·玻利瓦尔的忠诚继承者。为了完成玻利瓦尔当年的未竟之业,查韦斯上台后就宣布,他要以和平民主方式进行“玻利瓦尔革命”。
他指出,这场革命的思想来源有三个“根”:西蒙·玻利瓦尔;西蒙·罗德里格斯(前者的老师,主张人民受教育、自由、平等);埃塞基埃尔·萨莫拉(委内瑞拉独立战争期间的将领,主张主权归人民)。他把1999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称之为“玻利瓦尔宪法”,并把“委内瑞拉共和国”改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玻利瓦尔宪法”构建了查韦斯推进“玻利瓦尔革命”的法理基础。
2005年之后,他进而强调“玻利瓦尔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是年2月,他首次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8月,明确指出要实现一场“21世纪社会主义的革命”。他强调“21世纪社会主义”是委内瑞拉独特的社会主义,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印第安主义、玻利瓦尔主义、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的混合体。他说:“真正的基督比任何社会主义者都更加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耶稣是我们时代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强调社会主义而上台执政的他,像他的前辈阿连德一样,将去市场化推向了极端,把政府权力的触角伸向了各主要经济部门,用国家干预主义全面整合经济。具体举措包括:
其一,全面国有化。1999年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为国营公司。2001年的新石油法还增加了矿区使用费,提高了所得税,增加一系列新的企业消费税,打击与反对党过从甚密的委内瑞拉劳工联盟,引发石油工人大罢工,石油生产和出口几乎瘫痪。其结果,2万多名石油技术员工陆续被政府解雇。为实现“石油完全主权”,查韦斯自2004年以来,分步骤采取一系列石油国有化措施,最终将委境内全部油田收归国有。除了石油领域外,查韦斯还对电话、电力、水泥、钢铁、大米加工厂、咖啡、银行、超市等实行国有化。大规模的国有化赶走了外国投资者,也降低了本国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又产生了大规模的官商腐败和裙带交易。例如,2013年有8名委内瑞拉官员因从中委合作基金中挪用8490万美元而被捕,但该案至今悬而未决。新一届国会可能会对其进行彻查,以便对有关政府人员进行问责。
其二,价格管控。在查韦斯时代,政府为若干种基本食物制定了最高价格,严禁生产商涨价。马杜罗上台后,延续并强化了这种价格管控措施。政府对市场的价格干预破坏了资源合理配置,导致从黄油、咖啡、牛奶等基本食品到肥皂、洗衣粉、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再到药品和医疗器械,均出现物资供应短缺。当政府规定的鸡蛋和猪肉的价格远低于生产和销售成本时,商人们愤而摔破鸡蛋以示抗议。政府派出大量公务员和军人在全国范围内打击暴利经营的商家,占领多个大型家电、五金、汽车配件连锁店,逮捕非法涨价、投机倒把的商人。在有限价商品出售的超市,人们排起了长龙,商家不得不按身份证甚至指纹来定量配给。商店货架瞬间就会变得空空如也,政府则派遣士兵在主要市场把守,避免哄抢事件发生。由此也衍生了一个新生行业,人称“二道贩子”。二道贩子使用假身份证、贿赂商店保安、排队卖号等办法,每天如同工蜂一般,从一个商店到另一个商店寻宝、淘宝,然后加价售卖给没有时间排队的上班族。二道贩子是马杜罗最痛恨的敌人,将之称为“玻利瓦尔革命”的头号绊脚石,将倒卖物资的行为定性为有组织犯罪,予以严厉打击,但效果不彰。
其三,外汇管制。由于油价下跌、物资短缺,政府的外汇储备很快捉襟见肘。委内瑞拉政府对外汇实行严格的控制,使得一般老百姓和企业进口商品变得十分困难。马杜罗政府试图稳定货币,实施固定汇率并将汇率强行固定在6.3玻利瓦尔兑换1美元。但固定汇率需要大量的美元储备去冲销波动,提供兑换性和流动保障,委内瑞拉政府却没有足够的美元储备。因此,随着恶性通货膨胀加剧,黑市上的行情一路飙升,从最初的1美元兑换6.3玻利瓦尔发展到1美元兑换900—1000玻利瓦尔,仅2015年年内的涨幅就高达530%。政府也曾尝试推出中间汇率以遏制黑市汇率,但遭到惨败。
而他的所为,目标指向为社会政策的超福利化。委内瑞拉由于长期推行传统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造成贫富分化严重,为查韦斯主义的成长提供了温床。查韦斯和马杜罗的执政基础是中下层民众,采取一些亲穷人的再分配计划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它们走得太远了,大大超出其国力与财力的限度。按照委内瑞拉国家统计局的数字(INE),查韦斯政府在12年间(1999年至2011年)的社会项目投资达到7720亿美元。在此期间,社会投资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达到约60%,远远高于1986年至1998年期间几届政府所占的比重(约36%)。自2003年起,委内瑞拉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名目繁多、形形色色的社会计划,包括“罗宾逊计划”、“里瓦斯计划”、“苏克雷计划”、“深入贫民区计划”、“瓜依凯布洛计划”、“食品商场计划”、“住房计划”等等。仅就住房计划而言,2015年底前已经交付了第100万套住房,到2019年将交付300万套住房。这些住房都是免费提供给穷人,但居住者拿不到“房本”。如果他们不积极参加游行,不支持政府,就随时将这些住房收回。作为欧佩克成员国中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委内瑞拉国民享受着世界上最便宜的汽油——仅为成本的10%,比水都便宜。委人均燃油消费量是拉美各国平均值的3倍以上;平均每辆汽车的消费量约300公升。英国巴克莱银行此前发布报告称,按照官方汇率计算,委内瑞拉的汽油零售价仅为每加仑0.05美元;若按黑市汇率计算,该国公民仅需为每加仑汽油支付0.01美元。巴克莱预计,这一社会福利让委内瑞拉政府牺牲了近27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该国12.5%的GDP,以及超过90%的公共部门赤字。查韦斯和马杜罗曾多次尝试提高国内汽油价格,均因民众抗议而失败。
尽管查韦斯模式的社会计划短期内能够改善穷人的处境,但其负面效应非常明显。它只会让穷人不愿意通过个人奋斗摆脱穷困的处境,反而高度依赖政府慷慨的馈赠。更糟糕的是,要想持续获得穷人的支持,政府还必须不断维持并扩大这些福利政策,这从当前或长期来看都是不可持续的。今日之委瑞内拉之困已经证实了这点。
当然,查韦斯比阿连德幸运,阿连德在位仅仅3年时间,就被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所困的愤怒的人民逼到了总统府的墙角,最后被政变的军头所杀。而查韦斯不仅连续执政了14年,还得以善终。
那么,智利如何走出困境,又有哪些经验可供目前的委国借鉴呢?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民主的定义和标准来看,智利从此由先时的民主国家彻底的退化为军事独裁国家。军政权成立之后立即取缔了所有左翼政党,对被视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采用暴力镇压,一些非社会主义者的公开反对政府的民主人士也遭到迫害。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17年间,有多达2095人遇害,1102人失踪。而2004年,由“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大约有35000人声称遭到了军政权的酷刑折磨,而这其中有多达2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威权主义者皮诺切特镇压异己者的惯常办法就是严刑拷打。正是在这样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成千上万的智利人不得不逃亡到异国他乡。以现代视角的文明和民主、自由来看,皮诺切特无疑是野蛮的——排除异己,肆意践踏人权,这些不良记录可谓罄竹难书。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这个威权者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智利的社会经济状态却得到了全面的改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这显然与奥尔森的结论——民主有助于经济增长,根据字义我们完全可以将奥尔森的这一结论表述为,威权主义不利于经济增长——是不相符的。由于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80年代被其他拉美国家普遍称为“失去的十年”。但于威权主义统治者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却恰好相反,在这段时间里,该国的经济保持了强劲且持久的增长。米尔顿.弗里德曼将其称之为“智利奇迹”(The miracle of Chile)。
这一事实也再次表明,民主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在包括独裁在内的威权统治下,国家也可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也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做的讨论,包括独裁在内的威权统治亦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威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独裁国家的经济的增长呢?
正如事后验证的,这种现象跟这位独裁者所奉行的一种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政策不无关系。阿连德的口号是“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为模式的社会主义”。事实上,阿连德并不是教条的、死搬硬套列宁、斯大林理论,而是杂糅、融合了西方民主政体。正是这种智利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其治下智利在政治上保持了原有的民主、多元,但在经济上却完全践行着计划经济的那套——国有化、中央调配。而皮诺切特,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政治上采取的是典型的威权主义治理模式,但在经济领域则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的践行者。
他之所以走上经济自由主义这一道路,一群被成为“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的年轻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事件的当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曾引述Rosett的话写道“那些从芝加哥大学返回智利的学生,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摆脱困扰智利经济的停滞不前状态的一种办法。1972年下半年,当时阿连德的政策似乎已将经济推向崩溃.....(他们)开始制定恢复经济的计划。到政变发生时,他们已经完成了189页的初稿,其中既有调查分析也有解决方案,他们将这个计划交给(参与政变的)将军们。”
在开头的一年半时间里,这些将军们忙于对异见者的屠杀和对权力的争夺,而对经济问题毫无兴趣,就更不用说这一方案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镇压和杀戮之后,皮诺切特将军终于有兴趣来关注经济问题了,但一开始他也只是信任他手下的军人,于是将这个工作交给了军人们来负责。这些武夫弄弄枪、杀杀人还行,但要他们治理经济,真可谓是找个杀猪的来绣花一样,结果自然是一塌糊涂。从1973到1975年,通货膨胀一路飙升,危害变本加厉,再加上世界性经济萎缩的严重冲击,导致智利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这这种情况下,皮诺切特才记起那份经济方案,于是找到了“芝加哥男孩”,并请这些“男孩”中的豪尔赫.卡瓦斯(Jorge Cauas)、塞尔吉奥.德.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等人出马,到他的军政府里,担任财政部长、土地部长等要职,以此来全面负责智利的经济改革。

但在根深蒂固的国家干预思潮下,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并不顺利,军人们不满意于现状,但对于他们的改革却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们于1975年3月,将他们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的导师弗里德曼从美国请来,目的就是为智利的那么决策者和工商业巨头开讲座,进行洗脑教育,好为他们的政策的开展提供意识的基础。米尔顿.弗里德曼欣然的接受了这个邀请,前往智利进行了为期6天的公开研讨会。在这段时间里,这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宗师,配合着芝加哥男孩的方案,大力宣扬他的“休克疗法”,建议执政者的经济改革不要拖泥带水,而应大刀阔斧,譬如大幅度消减政府开支、放开物价、取消关税保护、吸引外国资本注入,以此来刺激本国产业在竞争中成长和壮大,以此来激活经济。他特别强调,面对着问题,执政者应该要有长痛不如短痛的心理,弗里德曼公开承认,采用这种办法,于短期而言,肯定会付出代价,如通货膨胀也许不会立马下降,但失业率却必然会上升。但正如戒除毒瘾一样,熬过了痛苦期,经济将会就此重生。
在会议中,皮诺切特与这位自由市场主义者有过一次长达45分钟的讨论,正如弗里德曼自己在笔记里所记录的:“他(皮诺切特)对休克疗法非常有兴趣....除此之外他没有表现出他本人和政府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强调并催促我在访问结束后,为他写一个意见备忘录。”
过后,弗里德曼也的确于其返回芝加哥大学之后“写出了我的看法。”他的看法是认同那些芝加哥男孩所得出的结论。弗里德曼认为他们这些被军政府邀请前往智利的学者的真实角色就是去审核芝加哥学生的结论,盖章并予以批准。“后来我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并且向公众和军政府推荐了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的核心就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就是打破原有的一切条条框框的约束,发展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他们走了一条与阿连德截然不同的路线,这包括采用休克疗法结束通货膨胀并恢复经济,同时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因为通货膨胀显然是因为政府需要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造成的。因此这也是结束通货膨胀、恢复经济至关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将养老金体系、国有工业和银行进行了全面的私有化改革。同时,降低部分税收,还废除了最低工资制和取消工会权利。由此,皮诺切特开创了智利经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纪元。
正是在这样的改革下,智利经济迅速恢复,并表现出强劲增长。通货膨胀率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下降到1980年代的不到10%。而1976-198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8%。实际工资与就业率也迅速上升,而失业率则出现明显下降。从1973年起到1995年,在这22年里智利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两倍半还要多,婴儿死亡率从6.6%下降到1.3%,而人民的预期寿命则从64岁大幅上升到73岁。由世界经济论坛所编制的“世界各国经济竞争指数”每年更新一次,2010年,智利排名世界第30位,在拉丁美洲排位第一,将第二、第三、第四的巴拿马(第53位)、哥斯达黎加(第56位)和巴西(第58位)远远抛在脑后。
最具可比性,自然也就最具借鉴性。于目前的委国而言,要想走出查韦斯困境,最好的路径,怕只有借鉴当年智利方案了——启用“芝加哥男孩”,全面实施经济自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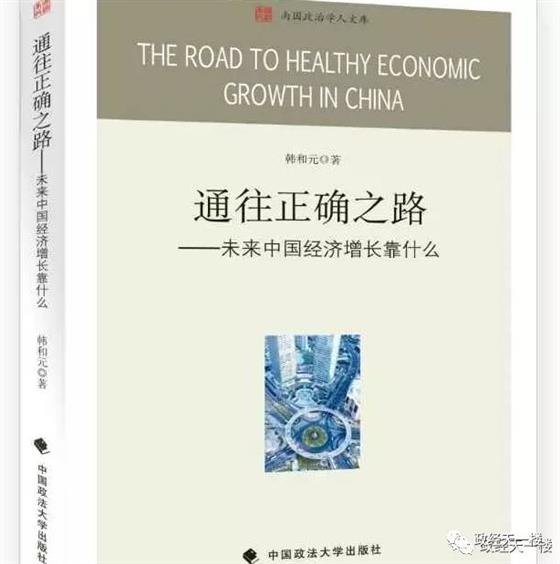
参考文献:
[1]韩和元.通往正确之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2]张根森.强权之灾,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失败”[DB/OL].共识网。转引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413/18/7442640_55035129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