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是已故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讲座教授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的代表作。英文版著作于199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经由陈兼、刘昶翻译成中文,三联书店出版后(1999年)[1],孔飞力及其著作渐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所知。本书以十八世纪人口压力下的清帝国为叙事背景,观察了一场为君主所想象的妖术危机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全书通过对社会环境、谋反与汉化、灵魂观念、君主与官僚制、底层民众的敌意等领域的深入剖析,讲述了一个重叠了皇帝、地方官员、普通民众等多个版本不同表述的政治事件。爆发于江南地区的妖术谣言不仅使普通民众暴露在被“叫魂”的妖术恐怖中,而且让远在承德避暑的乾隆帝误以为是颠覆满人的政治阴谋,坐镇地方的省级官员不得不应付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为此如坐针毡。《叫魂》对中文世界来说是意味深长的,此书不仅仅是对清中叶社会、制度运作的全景式鸟瞰,还包含着对后世政治运动的透视。作者利用大量奏折、档案、会典、实录,充分吸收了二十世纪美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为读者呈现了一部视野恢弘而论证详实、行文流畅而深入浅出的汉学巨作。笔者尝试在分析《叫魂》叙事结构的基础上,结合近些年的阅读心得,管窥孔飞力先生的治学方法与学术关怀,从而致敬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一、十八世纪清帝国的社会、经济与人口流动
“漫长的18世纪”对于欧洲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时代。经过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洗礼,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形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扩张与连接世界的商业网络,预示着一个崭新世界的到来。而十八世纪对于欧亚大陆东端的清帝国,同样是意味深长的。伴随着十七世纪政治、社会动荡的结束,清帝国迅速从频繁的战乱中恢复起来,和平孕育了人口的增长、商业的扩展与(官方资助)文化的繁荣。
从1700年至1800年,清帝国的人口从1.5亿增加到3亿。[2]清代中叶的江南在继承前朝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受益于外部白银的大量输入,“区域小市镇不断扩散发展”,“一个稠密的农村市场网络应运而生”[3](p34)。大规模的满蒙藏汉梵文的译经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预示着这个时代文化的繁荣发展。江南的经济又资助了清帝国的边疆开拓,对于帝国更为广袤的边疆,雍正帝任用鄂尔泰,将困扰中原数个世纪的西南诸政权纳入统一的国家管理体系,乾隆帝在继承父辈基业与武功的基础上彻底征服了准噶尔汗国,将其与六城一同变为大清帝国的新疆。即使在乾隆帝晚期的统治中,清代中央通过击退廓尔喀人地入侵、改革西藏行政制度、引入金瓶掣签规范活佛转世,强化了朝廷对西藏地区的经营与管理。十八世纪的清帝国奠定了近代中国的人口分布、商业结构与领土疆域。
那么孔飞力是如何观察十八世纪对于清帝国的时间意义的呢?在《叫魂》中孔氏重点分析了乾隆帝治下江南的社会经济与人口流动。不同于大陆学者对明清江南经济中“手工业工场”、“雇佣劳动力”的精心刻画[4],孔氏刻意避免了这种研究范式。他指出“像南京这样的地区性大都市里,确实有着不少大工场和大批城市劳工,但普遍存在于各地的则是一种复杂精细的外包工制度”。“他们可以居住在自己的村子里,同时却直接参与大生产体系的运作”(p39)。正如《正德华阳县志》所揭示的那样,“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之间。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着。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不卒岁室已空,其衣食全赖此。”[5]
这种农村—城镇市场网络与经济专门化生产的相互影响,塑造了“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6]的区域生产结构。在这种生产结构与市场网络中,即使人们住在自己村里,却直接参与大生产体系的运作。稠密的市场网络将各地的区域性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几乎使每个人都同某一市场有着固定的关系”(p42)。孔飞力指出,市场的密集连接也构建了全国性的信息网络,“关于各种地区性与全国性事件的消息见闻,也沿着连接各个村庄与各个市镇的商路,随着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传开去”、“中国各地的“小道”即便在那个时代便已同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信息网络联系在一起”(p43)。这种由市场网络构建的信息流通体系成为叫魂恐慌的重要传递渠道,百姓的恐慌、僧道的邪恶、官吏的腐败经由这些渠道,被商人、旅行者、僧道、乞丐绘声绘色地演绎后,从江南地区沿着运河、长江与官道,散布至全国。
在孔飞力看来,江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人口压力开始笼罩清帝国。不论是经济繁荣的长江三角洲平原地区,还是苏杭外围的广德[7]、徽州[8]等偏远山区,以及更为遥远西北甘陕地区[9],“生齿浩繁”成为了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美洲作物的引进与外界白银的大量输入,极大地延缓了人口压力所爆发的节点。“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适于在干燥高地上生长的作物…移植到难以灌浇的山坡地上”(p34),缓解了“米价日增”而带来的生存危机。而白银的流入使得“(米价上涨)对地方社会的冲击显然因货币供应的增加而得到缓和”(p44)。
孔氏指出,虽然白银的输入刺激了物价的持续增长,但在米价日增的同时,菜农、渔民手中商品的价格也出现持续上升。“在十八世纪的长期通胀过程中,投资者十分活跃”[10]。正如当时的观察者汪辉祖所揭示的“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对于米价上涨并未引起人们恐慌的原因,汪辉祖进一步解释道“今则鱼虾蔬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11]可见随着(输入)白银对地方社会的缓慢渗透,有效地缓解了当地人口激增所带来的人口压力。但汪辉祖的观察有着较强的地域性(萧山地区)约束,白银的渗入对普通百姓生计的助益能否有效辐射整个江南地区,以及更为广袤的内陆省份如何容受白银对地方经济生产的刺激,又如何在“生齿日繁”与“米价日增”之间保持经济发展的整体平衡,这些审慎的思考不由得让我们去反思白银供给缓解人口压力理论的普遍性。
对于清帝国整体而言,更常见的人口压力缓解机制则是由中心向边缘的开发式外向移民,以及各省府县随处可见的逃荒式人口流动。美国清史学者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在他(由博士论文整理而来)的著作《毛皮妆点的世界:清王朝治理下的野物、原始之地与自然边疆》(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7)中,在大量使用来自北京、台北、乌兰巴托的满、蒙、汉文档案的基础上,细致地观察了来自山东、河南、山西、直隶等地的汉人移民对满洲、蒙古地区的经济开发。虽然他们盗采口蘑、种植秧参、捕杀貂鼠的行径引发了与当地政府严重的暴力冲突[12],但开发式外向移民仍然是中原地区释放人口压力的重要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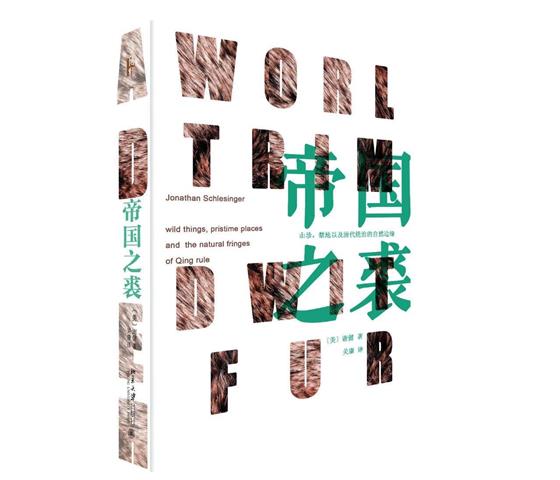
孔飞力也注意到清帝国在人口压力下活跃的移民现象“人口还移往处于长江与汉江流域的高地,移往满洲,移往很大程度上仍由土著居民居住的台湾,以及移往海外”,“曾经长满树木的山丘被开发成为勃勃发展的甜薯和玉米农场”,“在中国各地,人们都在向上或向外移动”。(p51)但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进行开发式移民的贫弱底层,白银的输入与移民的机遇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明显。反而“米价日增”促使大量被排除在农村市场网络、“大生产体系”之外的社会边缘群体不断向下层移动,构成了往返于长三角、运河、长江沿岸、官道的流民主体。人口压力与经济区域差异,促进了各区域之间人口的持续流动。
商人、僧道、乞丐等流动的人群汇集成浩浩荡荡的旅行者队伍,为“叫魂”妖术的想象提供了对象。外来者对社区生活的侵入加剧了民众对妖术的恐慌,这些恐慌伴随着市场网络所构建的信息传播体系,蔓延至整个大清帝国。
二、妖术危机的制度根源
在自由主义学者看来,1768年的叫魂谣言之所以能够动员清帝国的全体臣民[13],为一场被君主想象的危及王朝根本的“妖术危机”而神经紧绷,原因就在于过于散沙的社会长期经由国家的控制、改造,已经失去了自我治愈危机的能力。孔飞力沿袭了自由主义的研究范式[14],无论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中对地方精英与地方武装的精彩论述,还是《叫魂》中对国家强化社会控制的常规与专制手段的杰出分析,都可以管窥孔飞力的治学特色。透过叫魂案纷繁的文本记录,孔飞力观察到,普通民众、地方官僚[15]、军机大臣、皇帝对叫魂妖术的态度是极为不同的。那些构成叫魂案主要嫌犯的僧道、乞丐,在普通民众看来是侵入自己生活社区的危险陌生人。后者对这些外来者保持异常的警觉,他们通过妖术话语的想象,表达前者所带来的恐惧感。而在官方[16]看来,“任何不受控制的行为都带有某种危险性”(p56),“那些居无定所、没有家室的人也是无法纳入控制的人”(p55)。在这种先入为主的官方视角下,区域间流动的乞丐、不为官方所管理、控制的僧道[17],都是叫魂妖术的潜在嫌犯,唯一的区别就是后者更具攻击性,而前者起到的只是跑腿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不受控制群体的怀疑与忧虑,或许来源于更为古老的传统,并且产生于特定的政治结构中。国内学者秦晖将这种政治结构称为“秦制”,他从周秦之变中梳理出国家力量的激增与地方社会组织的萎靡,并借用谭嗣同“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的叙述,将自秦以后的中原的政治传统称之为“秦制”,其整体特征便是大共同体张扬而小共同体萎靡的“大共同体本位”。秦晖认为,秦制就是法家政治的理想图景,“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共同体,使专制皇权能直接延伸到臣民个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团体之阻碍”[18]。从清帝国对中原地区的民间结社、非正统宗教与宗法组织(“毁祠追谱”)[19]的打击来看,其行政控制与制度精神显然是对秦制的继承。1768年的妖术危机折射出了秦制对流动群体的攻击性,并且通过系统的礼法规范将其控制欲进行合法化。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对作为清帝国满洲特性象征符号的“辫子”的观察。叫魂妖术中丰富的政治意象,为孔飞力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观察视角。孔氏回顾了满洲征服年代“剃发令”的政治意义,指出“削发令本身成了满清皇帝用来测试臣民的一块试金石”,剃发与否已经成为汉人群体是否臣服清帝国统治的政治姿态。在清帝国征服中原的早期阶段,相比于“剃掉前额”,“辫子”并未上升为臣服满洲的政治意象。正如孔氏在书中所引述的吕书生与郭农夫之例,清帝国前期对头发的“关注”,更倾向于前额是否蓄发。然而剃发令的深入推行塑造了汉人群体的外观形象,原本不被重视的辫子逐渐代替“前额剃发”的象征话语,成为了臣服清帝国的形象符号。对此,孔飞力指出,“当某人已经留起当局所要求的发式以后,除非割去他的辫子,便难以通过他的发式对当局提出突然并具有象征意义的挑战(因为前额头发的生长是需要时间的)。很显然,要迫使别人因发式而卷入具有象征意义性的抗命,最容易的办法便是割去他的辫子[20]”(p77)。
当作为臣服满清统治政治意象的辫子为妖术逆党所割断时,乾隆帝逐渐将叫魂案与之前具有反满性质的“伪稿案”、“马朝柱案”联系在一起,并警示臣僚“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p197)。当这种新近的满人对汉民族主义的警惕与传统的秦制对自发势力的焦虑合流,乾隆帝重新定义了叫魂妖术的性质,“(孔飞力语:)叫魂妖党故意挑起剃发所包含的意象问题,意在谋反”(p199)。
在完成对清帝的国家—社会关系、满洲特性的象征符号、妖术相关的制度规范的精彩论述后,孔飞力沿着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思路探讨了叫魂妖术背后的官僚君主制。孔氏质疑了韦伯有关君主与官僚二者关系的论调[21],他指出,由于资料的局限,韦伯对于专制权力与法典化常规(codified routine)的认知是晦暗不明的,“(韦伯)实际上回避了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p247)。
在孔飞力看来,专制君主个人意志对常规权力持之以恒的渗透与改造,塑造了拘谨呆板的官僚生态。富有野心的君主面对官僚间权力庇护的网络时(“上下通同,逢迎挟制诸弊,皆所不免” [22]),试图通过秘密报告、宫中陛见、政治任命、礼仪行为来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信息情报网络。
文本的礼仪化互动强化了官员与君主之间的个人纽带,同时削弱了官僚常规权力独立解决公共危机的可能性。官员们面对主子的过分热情与反复无常,不得不回避风险,“最好的官员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员”。
上述的政治生态成为了复制妖术危机的制度土壤,君主对地方官吏的猜忌与苛责,激发了后者对前者的敷衍与搪塞。地方官吏在应付妖术案件中的无为与转移视线,又强化了妖术蔓延与官员失职给君主带来的危机感。在这种氛围中,对主子意志心领神会的富尼汉自然会迎合乾隆帝的危机想象,通过刑讯逼供疑犯充实叫魂妖术的真实性,“正是富尼汉的奏折及所附的供词使整个叫魂案持续炒作了三个月”(p238)。作为叫魂妖术至始至终首席原告的乾隆帝与配合主子演戏的地方官员,共同加剧了妖术危机破坏范围的扩大。
孔飞力最后探讨了作为“政治罪”的叫魂妖术,如何激发了普通民众的权力幻想。在对叫魂妖术危机下普通民众心态地观察中,孔飞力指出“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无论是慈相寺僧人因为妒忌而挑起的妖术谣言,还为了报复侄子而求助于石匠的沈士良,亦或是妖术危机发酵后将乞丐张四诬陷为剪辫犯的庄首赵某,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同却对着形形色色的对象宣泄着类似的仇恨,无论是亲人、债主亦或陌生人。“这是一场戏中戏,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做文章。除了丑恶的嫉妒,还又无耻的贪婪”。
对专制君主来说,普通民众对边缘群体的敌意,有效地补充了国家权力对后者的攻击力量。官方一旦认真发动对妖术的清剿(孔飞力语:“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p300-p301)。
在对“受困扰社会”生产敌意的原因分析中,孔飞力认为由于普通民众长期缺乏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去竞争所需的社会资源,朝廷更不允许民众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导致权力对于民众“通常只存在于幻觉之中”。这种将民众散沙化、原子化的统治策略,在巩固朝廷对社会控制的同时,瓦解了社会自我调节纠纷的能力,这也是民众利用官府对剪辫犯地清剿而报复他人的重要社会背景。在大共同体皇权政治的持续冲击下,传统的乡土共同体经受着朝廷“经纪”[23]、保甲制度的改造、非正统的宗教组织与民间结社遭受着朝廷的武断打击,地方社会的自治能力早已破坏殆尽。
这些被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称之为自生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小共同体[24],恰恰是能够治愈“受困扰社会”的良药,因为自治的宗族、宗教与民间结社,能够自然而然地为因血缘、信仰、兴趣、利益而凝聚在一起的群体塑造归属感,为人与人之间的重复博弈与信息对称提供互动的空间。这种重复博弈、信息对称与归属感极大地增加了普通民众互害的成本,小共同体内部的习俗和舆论不断约束着民众间相互攻击的勇气。缺乏这些小共同体的社会,当民众发生纠纷,权威的解决措施是诉诸于地方衙门,普通民众不得不直接面对冷冰冰的朝廷法纪。更重要的是,缺乏小共同体内部习俗和舆论的约束,互害而不承担责任成为了可想象的图景,而朝廷清剿逆党的决心为这种图景的实现提供了具体的措施。
需要补充的是,清帝国作为由内亚入主中原的征服王朝,本身存在着复杂多元的政治传统。站在历时性(diachronique)的角度审视清帝国的演变历程,从内亚一隅的部落联盟成长为欧亚大陆东端的大帝国,其本身就是对多种政治传统的吸收、改造与整合的过程。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探讨清帝国中的封建制与独裁制二者的关系时指出,满洲时代过渡至中国近世,实际上是“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复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从满洲时代的太宗,经过入关后的顺治帝直到康熙帝初年,清朝政权中出现了浓厚的封建色彩”。在这种满洲人的封建制度中,“宗氏虽然低天子一等,但其地位并非当时的天子所赐…天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子,是由于宗室承认了天子的地位。因此天子应当尊重宗室特权,同时肩负着保护宗室的责任”[25]。
国内清史学界有关满洲时代君主与八旗旗主共享治权的学术讨论非常多[26],并且随着清史学者满文阅读能力的整体提高,满洲时代的带有明显中古色彩的封建制度能够以更清晰的图景呈现。
《满洲实录》中所收录的努尔哈赤规划身后继承者的训谕,能够直观地反映这种贵族共治的政治精神。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27]
从中可以看出后金国努尔哈赤时代,贵族共治传统与精神的强大,就连努尔哈赤本人也深深受制于传统。
然而随着清廷入主中原日久[28],深受中原制度精神与统治策略的浸润,近世独裁制成为了清代君主压制满洲贵族地方自主性与统治权的不二选择。正如宫崎市定所提到的,“中国近世的独裁君主体制的理念不允许在君主与人民之间插入特权阶级”,因此无论是身份高贵的宗室、战功显赫的勋贵,还是科举遴选的汉人官僚,在君主眼中首要的义务就是绝对的忠诚与服从。
而那些与君主共享治权的贵族群体,本该是社会躯体中制衡君主权力意志的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却早已被专制权力改造为清帝国满洲性的粉饰。失去他们对专制君主激进决策的反抗,乾隆帝想象的危及王朝根本的妖术危机,就能迅速扩散,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三、超自然的对抗:妖术恐慌中的信仰与人心
有关叫魂妖术中人们对躯体与灵魂、头发与邪术、妖术预防法、施法群体的想象,孔飞力在本书中有着非常细致的观察。比如在第五章中,孔氏探讨了中国民间灵魂观念中的多种层次,他指出正是因为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以及“灵魂是既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又可以通过非自愿的手段而与躯体分离”(p133),所以才使得民众会想方设法“对可疑的妖党施行私刑,或者是诉诸法术来进行补救”(p142)。而作为拥有施法能力的工匠、僧侣、道士,尤其是居无定所的僧道群体,自然成为了民众怀疑的对象。
当这种对丢失灵魂歇斯底里的恐惧与底层冤冤相报的敌意交织在一起,朝廷的清剿决心自然能够激发人们相互迫害的热情。那些因为人口压力导致阶层下沉,而不得不向外流亡寻求生存的边缘群体,被裹挟进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敌意中。在前者看来,他们是不受国家管制、充满不确定性的治安危机的制造者。在后者看来,他们是掌握害人妖术、侵入生活社区的危险陌生人。
正如孔飞力所观察到的那样“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p159),“人们常常会将妖术同外来者连在一起…四处漂泊的流浪者由于在社区内缺乏联系纽带便很自然地成为了可疑分子”(p158)“‘好的’或‘安全可靠的’礼仪职事人员(为社区服务的僧道及巫师等)必须是社区的一员;而‘坏的’或‘危险的’职事人员(妖术人士)则从不会属于社区”(p160)。
孔飞力充分吸收了上世纪有关中国东南地区“招魂”仪式的人类学、宗教学的研究成果,在面对叫魂妖术中的民众恐慌时,他往往能够得心应手地将其与人类学、宗教学研究相结合。但不足之处在于孔氏太过于依赖国家—社会互动的分析模型,将妖术恐慌中的官方态度塑造的过于理性。仿佛饱读诗书的官僚与其病态多疑的主子面对妖术恐慌时,与愚夫愚妇们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精明理性,出于对政治安全、象征符号、国家信仰垄断的考量,本能地弹压来自各方的挑战力量。而后者愚笨无知,深陷于民间迷信的泥潭。
这种根植于国家—社会互动分析模型的刻板印象,往往不知觉屏蔽了极为关键的线索。比如乾隆帝的个人信仰。在本书第二章中,孔飞力在谈及官方对流动僧道群体的警惕时指出,“弘历从来就对佛教僧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并且孔氏将前者对佛教僧团剃发为僧的鄙夷与其接受的儒家教育联系在一起,“他(乾隆帝)的这种态度还反映了儒教对于那些‘甘心剃发为僧,并不顾父母其子,则行踪可疑’的人们所持有的更一般性的鄙视”(p57)。
考虑到本书的成书背景正是欧美内亚学与日本满学研究硕果累累的年代,孔飞力却没有利用这些前沿研究[29]。这种立足于中原本位视角而忽视了乾隆帝多元身份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显然是偏颇的。
乾隆帝是虔诚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信徒,无论他与三世章嘉活佛的亲密关系、对梵藏蒙满密教文献翻译的资助行为、积极营造藏传佛教风格的大型寺院,亦或死后陵寝中近百种的藏文密咒,都佐证了他的藏密信仰。
根据蒋扬活佛的著作《第六世班禅喇嘛传》中所披露的细节,乾隆帝在与六世班禅会面的过程中,乾隆帝不仅将“御用的仪仗、鞠、伞、宝幢、旗帜与御轿赠予喇嘛”。在六世班禅向乾隆帝献哈达,准备行下跪礼时,乾隆帝慌张地握住班禅喇嘛的手,并说了一句为此刻而努力准备的藏语:“还请喇嘛不要跪拜”。[30]
前来朝贡的朝鲜使节朴趾源在其所著的《热河日记》中,同样记录了乾隆帝对六世班禅上师的虔敬。为了让朝鲜使臣向六世班禅行拜叩之礼,“军机大臣初言皇上也(向班禅)叩头,皇六子也叩头,和硕额驸也叩头,今使臣当行拜叩。”对此,使臣反驳道,“拜叩之礼行之天子之庭,今奈何以敬天子之礼施之番僧乎?”但是当这些敬奉儒家信条的朝鲜使臣目睹了乾隆帝“两手执班禅手…相视笑语…一榻两褥,膝相聊也。数数倾身相语,语时必两相带笑含欢”[31],内心不免大失所望。上述他者的观察都细致地刻画了乾隆帝作为黄教虔诚信徒的形象,而不是如孔氏所言“弘历从来就对佛教僧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p57)。
事实上,乾隆帝私人的黄教信仰以及公开对佛经翻译、寺院修建的资助,为他赢得了信奉藏传佛教的藏人与蒙古人的“畏威怀德”。这与他所主张的“兴黄教以安众蒙古”[32]的政治战略互为表里[33]。与其说乾隆帝对佛教僧侣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倒不如说汉传佛教对于清帝国经营内亚的重要性微乎其微,并没有引起清廷官方的足够重视。
另一方面,乾隆帝对不被朝廷控制的僧侣的怀疑,同样可以在藏地的拉穆吹忠的身上看到影子。乾隆帝在承德了解廓尔喀人侵藏的经过后,派遣福康安率劲旅击退了廓尔喀人。并且决心改革拉穆吹忠降神确认活佛转世的宗教仪式[34],防止再次出现类似六世班禅兄弟三人都为活佛的现象。藏地拉穆吹忠降神占卜确认呼毕勒罕与中原“不法之徒假借僧道习俗,冒用祖师名义从事占卦预卜…从而吸引无知民众成为他们的门徒并非法结党”一样,触碰了乾隆帝对失控力量畏惧的敏感神经,“此等拉穆吹忠即系内地巫师,多以邪术惑人耳目”[35]。乾隆帝对待妖术危机绝不是出于无神论的理性质疑[36],而是对一切脱离朝廷掌握的未知力量(巫术)的焦虑。
因此,乾隆帝对汉地流动僧道的敌意绝不可能是儒家知识背景对剃发的鄙夷,因为前者的文化认同来源于内亚,并没有对发肤完整性的抽象想象[37],况且乾隆帝本身就是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佛。
四、江南与满洲:乾隆帝对中原与内亚传统的发明与想象
相比于祖辈们曾面对的强敌与叛乱[38],乾隆帝面临的政治危机可谓小巫见大巫。除上文所论述的朝廷对不被控制群体的焦虑与满人对汉民族主义的警惕,以及由此二者可能引发的谋逆外,弘历时代的危机还包括征服者们与汉文化深度接触后所导致的满洲特性地消失。比起前两者的直接冲击,后者的威胁更为隐蔽。
孔飞力强调汉化危机是左右乾隆帝评价地方官僚清剿行动的一条隐线,它加剧了君主对地方官僚的不信任感,并且强化了乾隆对汉文化的刻板印象:汉文化是堕落与腐朽的,它不断侵蚀着地方精英的正直、忠诚等美德,就连淳朴、坚韧的满洲武士也禁不住前者的腐蚀。“江南的乌烟瘴气渗入了各个层次,从省级大员到县级官员,无不为之波及”(p96)。当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刘墉向皇帝控诉江南地方政府对刁民、富绅与胥吏们的顾忌,“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县多所瞻顾,不加创艾”,官府们“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吏”[39]。对此,乾隆帝批示道“所奏实切中该省吏治恶习”,“近年封疆懈驰,直省中惟江南为甚”。在乾隆帝看来,“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构成了对满清政权最具威胁的江南陋习。
十八世纪的清帝国是如何塑造满洲的呢?不同于“堕落”、“腐朽”的汉文化,乾隆帝心中的满洲是原始和淳朴的净土。正如欧立德(Mark C. Elliott)在《乾隆帝》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乾隆帝心中“盛京是满洲神秘的发源地,尘封着满洲人的古老记忆”[40]。乾隆帝为了塑造满洲淳朴的风俗与古老的历史,在其自己所作的《御制盛京赋》中,颂赞了盛京的天地、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茂密的森林、肥沃的农田[41],以及淳朴的风俗“因周览山川之浑厚,民物之朴淳。谷上之沃肥,百昌之繁庑,洵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也”[42]。并且在他命人编纂的《满洲源流考》中,将“满洲清王朝的创立者与数世纪前女真金的创立者联系在起来”,旨在塑造满洲历史的古老性。乾隆希望《盛京赋》与《满洲源流考》能够丰富满洲的诸多传统,构建更稳定的认同感。
事实上,满洲“淳朴”、“原始”的形象同江南的“腐化”、“堕落”一样,都是乾隆帝的发明与想象。满洲概念的变迁与清廷对东北地区的经营相同步。最初的满洲概念[43],其空间范围大致等同于盛京地区。然而随着汉人流民对黑龙江、吉林、盛京地区资源的过度开采、满人汉化,以及沙俄东扩等问题的出现,引发了清廷对“东三省”治理的焦虑。
从1762年乾隆帝首次将三个地区[44]一体视为“淳朴之地”开始,满洲的概念迅速膨胀,原本等同于盛京的满洲,逐渐将(作为盛京藩篱的)吉林与黑龙江吸收进满洲的世界[45]。黑龙江与吉林地区多样、复杂的族群不得不被动接受清帝国所赋予的“满洲人”的身份,黑龙江中游的墨尔哲人(Merjele)、托科罗(Tokoro),松花江下游的吴扎拉(Ujala)、巴雅喇(Bayara),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齐雅喀喇(Kiyakare)、乌尔庚克勒(Urgengkere)、古法廷(Gufatin)、锡努尔扈(Sinulhu)等等[46],这些原本跟“满洲”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人群被历史遗忘、被“满洲”吞没。
对盛京地想象与对“东三省”地管辖开始重合,我们将这个地区称之为“满洲”。在这个过程中,清廷塑造了一种地域、族群和自然的新整合。朝廷一方面利用生态危机管束当地满洲人,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满洲地区。
那么清帝国又为什么要塑造江南与满洲呢?江南与满洲的形象塑造来源于满洲统治者族群特性的危机感。一方面,满语世界的征服者们在市肆、饭馆、剧院和官场与汉人世界的日常接触,使得形成于中原边缘的满洲文化开始暴露在一个更为悠久、浩瀚和丰富的文化面前。[47]“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p94)。皇太极对子孙们的担忧“子孙仍效汉俗”成为了乾隆帝最为头疼之事。
另一方面,那些自皇太极时代反复提及的男性美德(满:hahai erdemu)与满洲特性,逐渐衰落。可以想象,当乾隆帝目睹盛京的满人官员不能流利地用满语对话、八旗的满人武士骑射技艺不精、京城的满洲旗人流连于汉人的戏曲、对诗等中原文化消费,不免强化了对汉文化的敌意(即使弘历本身精通汉文化)。
最重要的是,作为皇帝忠诚臣仆的满洲官吏在中原官场传统的熏陶下,不免复制了康熙朝的盘根错节的权力庇护网络中,有着雍正朝整顿官场先例的乾隆帝,自然能够利用父辈的政治遗产,去重新改造限制专制权力的最后堡垒——常规官僚权力。正如孔飞力所提出的“这些朱批文字的背景是对妖术的清剿,但其内容则涉及到官僚的控制”(p290)。因此对乾隆帝来说,汉化的焦虑与失控的妖术都是一场针对王朝根本的危机,前者腐蚀了满洲精英,而后者试图颠覆满洲的统治。
专制君主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发明与想象,反映了背后的文化偏见与其权力意志的绝对化。专制君主可以根据心中喜好,设计不同群体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认同,而被设计的群体会在本地传统与前者的发明与想象中找到妥协。这种设计者与适应者对立的背后,是一种缺少中间组织制约中心的社会图景。努尔哈赤时代君主与八旗旗主共治的黄金时期早已结束,利用中原传统打击八旗旗主的皇太极与建立私人信息网络破坏常规官僚政治的胤禛已经为弘历时代政治运动的滥觞构建了制度路径。乾隆帝的病态多疑与反复无常是制度精神结出的果实,那些能够抑制前者的小共同体早已被朝廷所抹杀。
五、远去的孔飞力及其时代
孔飞力出生在一个美籍犹太裔的记者家庭[48],本科期间在哈佛大学学习“东亚文明史”(Introduction to East Asian Civilization)课程,以及跟随父亲去日本旅行的经历,让孔飞力对东方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49]后来在入伍期间于蒙特里军事语言学校(the Army Language School at Monterey)学习中文,复员后回哈佛大学跟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学习中国历史。并凭籍着《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50]一书,为美国汉学界所认可[51]。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各地档案馆、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的对外开放,吸引了孔飞力这样的海外中国史研究学者前来访问交流。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北京访学的孔飞力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接触到乾隆朝“剪辫案”的档案材料[52],这次“邂逅”成为《叫魂》一书的起点。《叫魂》为孔飞力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望[53]。
他创作的四本著作[54]与大量论文,为后世的研究学者留下了广袤的思考空间。学人们如何利用他留下的这些史学遗产,如何继承他未完成的学术研究,又如何理解他对中国现代性的回应。这些深入而有意义的思考将会成为我们了解上世纪美国汉学学术传统绕不开的话题。令人惋惜的是,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四年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叫魂》的中文译者之一陈兼先生追忆时指出,“孔飞力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很孤寂的。他从哈佛退休后,人一走,茶就凉,渐渐被遗忘”,“孔飞力和魏斐德、史景迁一道,被称为他们那一代中国史研究学者中的‘三杰’。前几年,魏斐德先生走了。前两年,孔飞力先生也走了。中国史研究‘三杰’,走了两杰,走入了历史…不禁想到,这是否意味着那个曾属于他们的时代的终结?”[55]
注释:
[1]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2] 参见[美]何秉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78页//转引自孔飞力:《叫魂》,第51页;[美]欧立德(MarkC.Elliott):《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4页。
[3] 孔飞力:《叫魂》,第34页。
[4] 参见孙竞昊:《明清江南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性能探析》,《江汉论坛》1997年01期;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手工业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04期;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05期。
[5]《正德华阳县志》,转引自孔飞力:《叫魂》,第38页。
[6]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63页。//转引自孔飞力:《叫魂》,第37页。
[7]参见《广德州志》(1881年版),第24卷第10页。//转引自孔飞力:《叫魂》,第48页。
[8]参见汪士铎:《汪梅翁乙丙日记》,文海出版社(台湾)1967年重印本,第1册第13页,第2册第10页。//转引自孔飞力:《叫魂》,第49页。
[9]参见全汉昇:《乾隆十三年的米贵问题》,载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新亚研究所(香港)1972年版,第560页。//转引自孔飞力:《叫魂》,第44页。
[10]韩书瑞、罗斯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第222页。//转引自孔飞力:《叫魂》,第36页。
[11]参见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乾隆五十九条。//转引自孔飞力:《叫魂》,第46页。
[12][美]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关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8-91页。
[13]包括军机大臣、各省督抚、地方官吏、普通民众,以及叫魂案主要怀疑对象的流动僧道、乞丐等。
[14]参见陈兼:《追忆孔飞力③:远去的他的时代》,《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8-02-10.https://mp.weixin.qq.com/s/7L7xfgTMP9BAGK_tftLFdQ
[15]指各省督抚、地方官吏。
[16]包括君主与各级官僚。
[17]参见孔飞力:《叫魂》,第151。“他们既不受宗教纪律的约束,也不服从国家的控制管辖”。
[18]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19]参见[清]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十一《复宗法议》,清光绪二年冯氏校邠庐刻本。“公于乾隆中年抚江西,有此令,未及成而去。继之者,以他岳连及祠戸,遂一律毁祠追谱,与公意正相反”。
[20]为此,孔飞力援引了《洪业》中的例子,“反清志士强行割断遵从满清法令的农民的发辫。”参见孔飞力:《叫魂》,第77页。
[21]韦伯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
[22]《大清十朝圣训》,第92卷第3页(1749年)。
[23]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24]哈耶克认为,“自生秩序“(Spontaneousorder)是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这种秩序是人类群体自我生成或源于内部的秩序;它不因计划或设计而成,是人的行动而非设计的结果。参见[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52-58页。
[25]参见[日]宫崎市定:《雍正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题解:雍正的时代。
[26]参见杜家骥:《清入关前的分封制综论》,《学习与探索》1998-06-23;杜家骥:《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史学集刊》1997-05-30;杜家骥:《顺治朝八旗统领关系变化考察》,《南开学报》1996-09-20.
[27]《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28]皇太极时代就已经加速了君主权力的扩张,但由于后金国制度根基立足于八旗组织,贵族政治仍然富有活力。
[29]例如[美]DavidM.Farquhar.“EmperorasBodhisattvaintheGovernanceofCh’ingEmpire,”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38,No.1,1978,pp.5-34.在这篇论文中DavidM.Farquhar率先提出“作为菩萨的皇帝”这一议题,并探讨了乾隆帝菩萨形象的源流,以及对清帝国统治的重要意义。
[30]参见「日」平野聪:《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现代东亚如何处理内亚帝国的遗产》(大清帝国と中华の混迷),林琪祯译,八旗文化,2019年。
[31]参见[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1997年,185-186页。
[32]参见《喇嘛说》
[33]乾隆帝在《喇嘛说》中将自己修习藏密仪轨与经营蒙古的政治战略联系起来,“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
[34]1792年乾隆帝在给福康安等人的谕示中指出“向来藏内出呼毕勒罕(转世灵童),俱令拉穆吹忠降神附体,指明地方,人家寻访,其所指呼毕勒罕不止一人,找寻之人各将所出呼毕勒罕生年及伊父母姓名一一记明,复令拉穆吹忠降神祷问,指定真呼毕勒罕,积习相沿,由来已久。朕思其事,近乎荒唐,不足凭信。拉穆吹忠往往受人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而藏中人等因其事涉神异,多为所愚,殊属可笑。此等拉穆吹忠即系内地巫师,多以邪术惑人耳目。而拉穆吹忠降神时,舞刀自扎,身体无害,是以人皆信之。此等幻术,原属常有。但即使其法果真,在佛教中已最下乘。若使虚假,则更不值一噱。其妄诞不经,岂可仍前信奉?福康安等现在整饬藏务,正应趁此破其积弊,莫若在藏即令拉穆吹忠各将其法试演,如用刀自扎等项果能有验,则藏中相沿日久,亦姑听之。若福康安亲加面试,其法不灵,即当将吹忠降神荒唐不可信之处对众晓谕,俾僧俗人等共知其妄,勿为所愚。嗣后出呼毕勒罕,竟可禁止吹忠降神,将所生年月相仿数人之名,专用金奔巴瓶,令达赖掣签指定,以昭公允”参见[清]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乾隆一百十六,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35][清]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乾隆一百十六,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36]正如上世纪藏学家牙含章在《班禅额尔德尼传》中所指出的那样“清高宗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也承认人死以后‘灵魂’继续存在,而且还可以‘投胎转世’”。参见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华文出版社,2001年。
[37] 女真人的剃发与剺面传统。
[38] 皇太极之于林丹汗,福临之于多尔衮,玄烨之于鳌拜、三藩、噶尔丹,胤禛之于诸贝勒、噶尔丹策零。
[39]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95页。
[40] [美]欧立德(MarkC.Elliott):《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4页。
[41] 欧立德:《乾隆帝》,第84页。
[42] 参见《清通志》卷三十四都邑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制盛京赋有序》。
[43] 1636年,皇太极宣布今后将使用“满洲”这一新称替代传统的“女真”称谓。
[44] 黑龙江、吉林、盛京。
[45] 1803年,嘉庆帝宣布“东三省”是王朝的故乡,乌拉(即乌苏里江上游的“打牲乌拉(满:butha ula)”)“皆系满洲”;道光帝延续了这种思路“我朝根本重地”;通过《圣武纪》等文献的传播,满洲=“东三省”的观念开始为官方与学者共享,并在19世纪广泛流行,且多次出现在官方文献汇编、地方志、游记和史书中。参见谢健:《帝国之裘》,第71页。
[46]参见[美]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关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9-50页。
[47] 欧立德:《乾隆帝》,第80页。
[48]虽然孔飞力本人出身在英国伦敦,但他们祖父母早在19世纪40年代分别从德国和奥地利移民至美国。“他的父亲虽出生于美国,却长期担任《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而侨居英伦”。参见李明欢:《孔飞力的中国移民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16年09版。
[49]参见周武:《孔飞力生前未刊专访: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社会》,《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03-01。https://mp.weixin.qq.com/s/909urfU8AZ6jzrnFooiSSg“我作为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选修了费正清和赖肖尔(Reischauer)先生主持的“东亚文明史”课程,之后我便对此深感兴趣。大约与此同时,我随着我的记者父亲到日本旅行,从此对学习日本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50]即孔飞力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MilitiainChinaDuringTaipingRebellion:TheTheoryandPracticeofTuan-lien)。
[51]该书成为孔飞力执教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的“敲门砖”。
[52]参见陈兼:《追忆孔飞力②:翻译<;叫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8-02-09.https://mp.weixin.qq.com/s/_-hhZsjMeg_9F27hGjEXng
[53]《叫魂》于1990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列文森奖”。
[54]即《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
[55] 参见陈兼:《追忆孔飞力③:远去的他的时代》,《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8-02-10.https://mp.weixin.qq.com/s/7L7xfgTMP9BAGK_tftLFd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