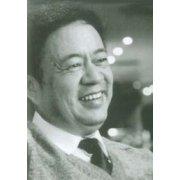一
我常常思念着故乡的灵魂,榕树。
记得有人问:你追求过怎样美丽的灵魂?我说,榕树。
情感的潺潺,思想的潺潺,再一次流过故乡崎岖的山野,再一次流过往昔峥嵘的岁月,回过头来想想,那昨天使我爱恋过的灵魂,今天依然让我向往着的灵魂,也只有它——榕树,我的永恒的爱恋。
二
我思恋的榕树,不知道使多少陌生人为它兴叹过,倾倒过。
真是太壮阔了。只要你靠近它,就会感到它的全身都充满着一种最动人的东西,这就是生命。
善于思辨的哲学家说,美就是生命。我相信,因为榕树,我才相信。
几乎是整个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我都在观赏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