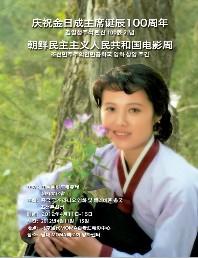
百老汇电影中心正在举办“朝鲜电影周”,电影旨在“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0周年”。我看了《桔梗花》这部电影,比想象中要好,画面和人物让我想起中国八十年代的老电影所呈现的气质:蒙昧,单纯,淳朴。观影过程中好几次湿了眼睛,因为演员的表演实在太真挚感人,以至于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蒙昧的反人性的故事,仍不禁被其中绽放的心灵之美、之痛所打动。
影片采用倒叙手法,以一个老人带着儿子回到故乡“赎罪”的悬念开始,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松林是村里最美的姑娘,她和村里最有才华的小伙子元峰深深相爱了。然而元峰讨厌贫穷、落后的家乡,他厌烦了没有尽头的艰苦劳作,以及那遥遥无期的拥有电灯、白米饭、肉汤的“共产主义生活”蓝图。当他得到去城市生活的机会想带着心爱的姑娘一起离开时,松林拒绝了,她认为这等于嫌弃和背叛家乡,是可耻的行为。她希望元峰和她一起把贫穷的家乡建设成富饶的家乡。但元峰并不认可她的幻想。他作出痛苦的抉择,还说了一句让全世界姑娘都心碎的话:“在爱情和追求自己的理想抱负之间,我宁可抛弃爱情。”就这样,相爱的人儿分手了。他们彼此苦等了对方五年,元峰期待松林能改变主意和他去城里,松林则相信他一定会重返家乡。五年后他们再度相逢在火车站,元峰买了两张火车票。但,二人再次不欢而散。从此,松林憋着一股倔强的火热的劲头没日没夜干活劳作,和父老乡亲一起建设家乡,最终在一次罕见的暴风雨中为抢救国家财产——一只小锦羊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元峰则在人生的晚年,带着儿子回到家乡,用让儿子回到家乡扎根的方式进行他人生的“赎罪”。
“桔梗花”作为一种默默开放在深山里的花,代表了女主角松林姑娘,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她的美丽、纯真、忠诚、勤劳、无私,即使作为观众席上一名“新时代女性”,我仍无比喜爱她的朴实美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主题思想”引领下,松林姑娘曾说过“总有一天,他会明白幸福不是他那样……幸福是为建设自己的家乡艰苦奋斗而结出的硕果”之类“点睛”的话。按这种思想,松林属于“胜利者”,因为她曾经的爱人终于在人生的结尾作出“赎罪”的忏悔。可是,她真的是胜利者么?她的坚持是对的么?幸福是不是只能有一种标准答案呢?那离开家乡去城市实现理想的元峰在家乡之外所做的贡献就不能算作贡献么?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影片要引导人们相信离开贫穷的家乡追求更富裕美好的生活就是叛逃者和罪人?毫无疑问,“故乡”在影片中只是隐喻,无条件地效忠国家才是真正的目的——不要嫌弃朝鲜,不要被外面的花花世界勾引,所有为个人意志与幸福而离开国家的人都是可耻的叛徒。
元峰的儿子在家乡父老乡亲面前下跪及痛哭流涕的那一幕令人震撼和悲伤,这等于说,那曾经在他父辈身上燃起的微弱而痛苦的觉醒之火,终于已经完全浇灭。统治者胜利了。那因蒙昧而忠心归顺的薪火将继续相传,代代相传。
观影过程中我心情沉重,有点悲伤。所有扭曲人性混淆概念迷乱心智的统治手法何其相似:一只小绵羊被置换成神圣不可或缺的“国家财产”,一个诡异的统治者被宣贯成“慈父领袖”,一个掐断自我幸福泯灭人性需求的女人被一步步送上“英雄”的宝座,那些勇于莫明其妙的牺牲与奉献的“英雄人物”被官方给予高高在上的荣誉、赞美和歌颂。所有女性都被抽离掉女性特征——近乎男式的灰色制服、严肃僵硬的表情、与男人无异的艰苦劳作……一切关乎个人的爱与美在影片中芳踪难觅、转瞬即逝,只有集体利益概念和忠心爱国的观念被无限强调与夸大。
在亚洲圈,还有另一个国家面临和朝鲜程度不一但性质相同的灾难与困境。所以,当看到朝鲜电影中所呈现的令人发指的匮乏、蒙昧和荒谬时,我们不必心生优越,因为至少可以猜测,朝鲜人民对他们所承受的一切苦难及背后的真相了解少得可怜,甚至完全缺失,因而他们的蒙昧中仍有打动人心的纯真。可我们不是,我们早已看到这个国家的真相,也早已在拜金主义的堕落中失掉纯真,我们盛产比朝鲜民众更可怕的东西——明了真相但仍无所作为的深重而精明的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