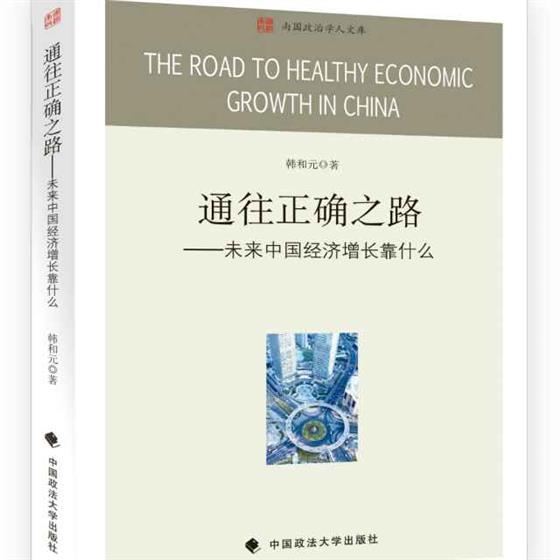摘要:商鞅们有他恶的一面,譬如愚民弱民政策,譬如一些法西斯举措。但他们在恶的一面之外,又确实在打击和限制特权阶级方面,在给人民赋权方面,做出过不懈的努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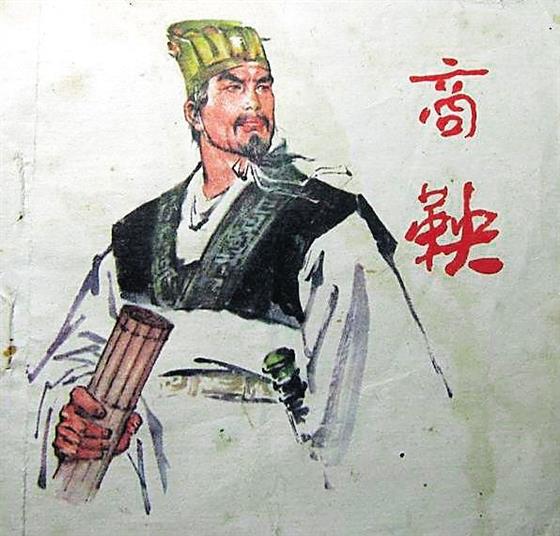
主流的观点认为,商鞅和他代表的法家,是法西斯主义者,而他的《商君书》简直就是一篇毫无人性的法西斯式的政治理想书。对于这种论调,个人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正如本文标题所示,我甚至认为商鞅和他的法家老师们,甚至可以算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权主义者。
这里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何谓民权。孙中山早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曾撰写《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文章提出清政府“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次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制订《革命方略》,解释建立民国,在于使“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平均地权,其要旨在使“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是首次明确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之主张。由此可见,所谓的民权即是指,打破特权阶级的权力和利益的垄断,从而让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利。
根据这一定义,纵观中国历史,真正打破特权阶级的特权,真正赋权于民的大努力大约有三次。第一次便是商鞅和他的法家老师,关于这点我们于下面再进行详细论述;第二次是隋文帝杨坚的科举制度,他让寒门通过念书也可获得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第三次就是清末以来,欧美自由民主概念的东来。
商鞅可谓是改革家中的集大成者,他的变法其实就是在总结了春秋末年晋国六卿改革、前期李悝改革和吴起变法的经验,特别是李悝的改革而提出的。正如我曾在《秦国改革启示录》一文里提及的,秦国的商鞅变法,几乎没有原创,秦国人只是通过后发优势、通过拿来主义,将人家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而已。甚至连商鞅的徙木立信秀都是抄来的,抄谁的呢?吴起的,《韩非子·内储》记录了个“倚车辕”的故事,说吴起让人将一个车辕放在路边,然后下告示,说如果谁把他搬到了指定位置,那么将予以重赏。而其思想的主要源头还是在于李悝,史书就有说他好李悝之教。

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商鞅曾在魏国的国务院工作过,而李悝就是之前的总理。从李悝改革到商鞅入魏,不过几十年而已。李悝的那套东西,肯定还有遗存。商鞅对这些东西不但是耳濡目染,而且还衷心佩服、勤加学习。《商君书》在这方面的材料,为数甚多,比如《算地》、比如《徕民》无不透着李悝“尽地力之教”的影子。而《商君书》可以说,集中的体现了商鞅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及经济政策、法治原则等。后来,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来投奔秦国,而来时就携带了一本李悝的《法经》。从这里可见,他跟李悝一样,非常清楚,如果要想确保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那么就必须得建立起法治体系。商鞅和他的老师们的改革的内容,无不涉及打击特权阶级。
打击特权阶级——夺淫民之禄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这本书里所阐明的,生产力固然决定着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反过来亦可制约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李悝经济改革的深入,这种制约现象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严重。这时如果想要生产力得以继续发展,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深化改革,以此让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无论是李悝还是吴起或是商鞅的改革之刀,无不砍向了这种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上层建筑——奴隶主贵族赖以依存的爵禄世袭制。爵禄世袭制又叫“世卿世禄”制,这里的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禄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财物。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世袭卿位和禄田的制度在古代曾十分盛行是奴隶制时代奴隶主贵族世代享有其祖上获得的爵位、官位以及相应俸禄的制度。
这种制度有两种极大的弊端,一是阶层固化所造成的社会工作及生产效率的低下。世卿世禄制是一个真正意义封闭的制度更是一个拼爹的制度,由于新鲜血液不能流入,从而导致缺乏竞争。那些贵族们的子孙生下来就可预见他们的未来,因此整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由于长期养尊处优,骄奢淫逸,他们居官不谋官事,为国不念国政,不仅不能为国家带来尺寸之功,还要消耗大量国家财富。同时,由于社会板结、阶层固化,这种制度更是堵塞了一大批渴望建功立业的有志之士的上升通道。
对于这种制度的危害,无论是李悝吴起还是商鞅,都是有着很深认识的。譬如李悝就将那些仅仅因为出生的好,而居官但却不能谋官事,不能为国家带来尺寸之功的贵族称之为“淫民”。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记载了他跟魏文侯这样一段对话,有一次魏文侯问他:“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呢?”他的回答就说:“我听说治理国家的方法:给付出劳动的人食物,给建立功勋的人俸禄,任用有才能的人,并且要赏就要实行、要罚就要得当。”还站在传统意识上的文侯就难免惊诧了:“我赏罚都得当,但是百姓还是不归附我,这是为什么啊?”李悝回答道:“是吗?那大概是国内还有大量的‘淫民’吧! 我听说:只有取消了这些‘淫民’俸禄,才能招揽于国有利的有志之士。父辈有功享受国家的俸禄是无可厚非的,但他的后辈没有功勋却享受着父辈的待遇,出门就乘着车马、穿着华美的衣衫,算得上荣华富贵;在家则沉迷于竽琴钟石一类乐器,正因为这种制度,打乱了乡里的礼教。像这样的人,就应该取消他们的俸禄,拿着节省下来的钱去招揽国家的有志之士,这就是所说的剥夺‘淫民’。”
李悝向爵禄世袭制所发出的挑战,是在动摇奴隶主政权的上层建筑。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他无疑要付出了巨大的勇气和智慧乃至牺牲的决心的。但仅仅只有李悝的努力和付出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一个新制度的建立能否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最高权力者的决心。为解决当前的各种问题,被任命来建立新制度的主持者,往往是外聘的新人,这些人才哪怕才华再高,也很难有力量吸引或强迫旧权力层的合作。这个时候真正能够负起全部责任的,就只有最高权力者而已了。所幸的是,李悝遇到了好老板,他的建议被魏文侯全部采纳。在魏文侯的强力支持下,在李悝的精心策划和认真执行下,在魏国,贵族们的特权被逐步的取消了。国家建立起了一套依靠战功和才能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从而使得一大批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乃至有作为的平民,通过李悝和魏文侯所架设的阶梯,得以进入权力中心,整个社会由此得以对流,社会活力得以彻底激活。
吴起在楚国的改革时,其重点也在于剥夺贵族特权、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正是因其体认到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封君太众”,这些封君们“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对“三世而收爵禄”,就是说,你所封到的地、你所享有的俸禄,只可以世袭三代,三代之后,国家就要全部收回。同时规定,废除疏远贵族,也就是那些跟国君血缘关系比较远的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停止对其按例供给。降低贵族——尤其是大臣和封君的爵位,缩小他们的领地,减少他们的属民。李玉洁教授在其《楚史稿》里指出的:“吴起变法,目的是富国强兵。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均平爵禄,消灭世卿世禄制度,奖励耕战,任贤使能。吴起变法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李悝和商鞅的改革。

而于秦国,商鞅在第一次变法时,则明确约明:“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句话隐含着两个意思: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他们的特权,重新分配。换句话说,就是自法令执行之日起,所有旧爵秩全部收回,旧贵族全部沦为百姓,他们要想重新列籍贵族,那么就得跟其他普通百姓一样,得到战场上去奋勇杀敌,通过立功才能得到新的爵秩。
当然,在打击特权阶级,瓦解其对权力和利益的垄断之外,商鞅们还积极地为人民赋权。譬如商鞅变法时,其新法就明确规定,只要有军功的,不管身份尊卑贵贱,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这就充分的体现了,在福祉方面,国民可平等以享之。除此之外,政令还明确规定:凡勤于耕织、生产粮食和织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
当然,商鞅们之所以大力打击特权阶级,还有一个现实原因,那就是这些特权者很容易对君权构成威胁。根据当时的制度,一个卿一旦被正式分封,那么他就有其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官僚体系,自己的武装。一旦势力壮大,君主根本就无力去约束和控制他。韩赵魏三家其实就是通过世卿世禄这种制度而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断于法
此外,商鞅们还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在打击特权阶级,给人民不断赋权的过程中,李悝还在法律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集前朝和各诸侯国法律之大成,再根据魏国的具体情况,编制了《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
首先他是一部私有制法,“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晋书.刑法志》)”是该法的立法之本。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时候的“盗”和“贼”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盗”和“贼”多少是有些出入的,这个时候的“盗”主要是指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而所谓“贼”,主要是指对人身的侵犯,包括杀伤之类。
当时的魏国奴隶制残余十分严重,没落的奴隶主贵族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不断地进行破坏性的活动。《法经》关于惩治“贼”的规定,矛头主要就是针对奴隶主贵族的。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主贵族可以杀害奴隶、迫害新兴地主而不受法律的约束和制裁。《法经》则宣布任意杀人是犯法的,要治罪处刑。从而限制了奴隶主贵族的暴行,打破了保护奴隶主贵族特权地位的传统。此外,于《杂法》中提到的“狡禁”和“城禁”以及严禁议论国家法令的规定,也包括有打击奴隶主贵族复辟活动,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含义。
李悝为了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保护私有财产及其统治地位,因而把惩罚“盗”“贼”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排在最开头的《盗法》、《贼法》就是专讲侵犯私有财产、人身伤害的犯罪行为及惩治办法的,对于人身伤害,相关法律的规定是:杀人者当诛,此外还将籍其家。虽然刑罚过于残酷,但这种保护私有制、以确立崭新生产关系的决心是跃然可见的。
同时,该法典也是我国最早的《反贪污法》,法典明确规定严禁贪污受贿,如有违反,将军将被处死,如果是丞相,虽不被处死,但必须将其助手处死(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也是我国的第一部反赌博法,这个法律的最大特点是,官位越高的受到的处罚越重。法典规定:博戏罚金三市,太子博戏则笞,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一般人赌博的话,将被处以罚款,但对于太子这样的位高权重的人而言,罚金根本算不了什么,必须采用更为严厉的方式,如果是太子触犯该法,就将面临现在新加坡很具特色的鞭刑,如果受了鞭刑再犯则处罚加重,如果第三次再犯很可能的结果是废掉太子之位而另外再立新太子。
这一点为商鞅所继承,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年幼的太子触犯了新法。只是考虑到太子毕竟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更重要的是,以太子当时的年龄而言,如果没有人唆使和故意纵容的话,是断乎不可能犯此大罪的。于是,商鞅处罚了太傅公子虔,这个公子虔就是秦孝公的庶出哥哥,又以黥刑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孙贾。
当然,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这种“法”无疑是提供给统治者用来统治民众的,是统治者拿着刑法去治理国家而已,是一部政治压迫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这些法治举措,在当时那个时代所确定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进步意义。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于经济体制上,法典对私有产权所进行的保护。这为“废井田、开阡陌”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提供了法律意义上的确认和保护;其次在于政治制度上,《法经》所追求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一目的,就是旨在于取代奴隶制时代的“礼治”。因为一旦确立了“法治”,“刑不上大夫”的局面就将被打破。这也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于制度上,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最后需要予以说明的是,我们讲这些,并不是要给商鞅们翻案。商鞅们有他的历史局限,有他们恶的一面,这个没啥好反对的,譬如愚民弱民政策,譬如一些法西斯举措,给他们翻案是没有必要的。我想说的是,正如前面所论,他们在恶的一面之外,又确实在打击和限制特权阶级的权力和利益垄断方面,在给人民赋权方面,做出过不懈的努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如美国开国国父华盛顿们一样,他们从没有给予过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以自由和民主,乃至从没有将其当过人看,但这并不构成,我们就此否定他们是先贤的正当理由。
本人最新出版专著《通往正确之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书,在部分图书销售平台已经上架,敬请各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