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起哄哲学的争鸣与研究——
一个非圈养哲学家的正传
文/曹喜蛙
本文原载《法律与生活》杂志2008年12期
题记:《中国青年报》2006年04月18日刊登了本报记者黄少华的文章《我是哄客我在搅动网络江湖——朱大可、展江、曹喜蛙如此说》,2007年11月21日财经类网站价值中国网刊登了该网记者覃怡敏与曹喜蛙的采访对话《谁都不可能在网上做甩手掌柜》,同月上海的《服饰文化》杂志又刊登了该杂志记者胡悦薏与曹喜蛙的采访对话《从边缘人到互联网哲学家》,这些记者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采访,至今没有互相见过面。可见当时在网上起哄理论在网友中受热捧的状况,到2008年7月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该书《赢在互联网》,12月《法律与生活》杂志邀请我写了《一个非圈养哲学家的正传》这篇文章,这是司法部主管、法律出版社主办的权威媒体。从此起哄哲学正式从网上走到各大纸媒,甚至大学客堂,甚至走写进国内外的硕士、博士论文。至今一听起哄哲学依然有人嗤之以鼻,起哄哲学也并没有开过专门研讨会,但是却有诸多学者专文讨论,该理论抓住了互联网时代一大矛盾和解决方案,俨然网友真的都拥有了上帝赋予的起哄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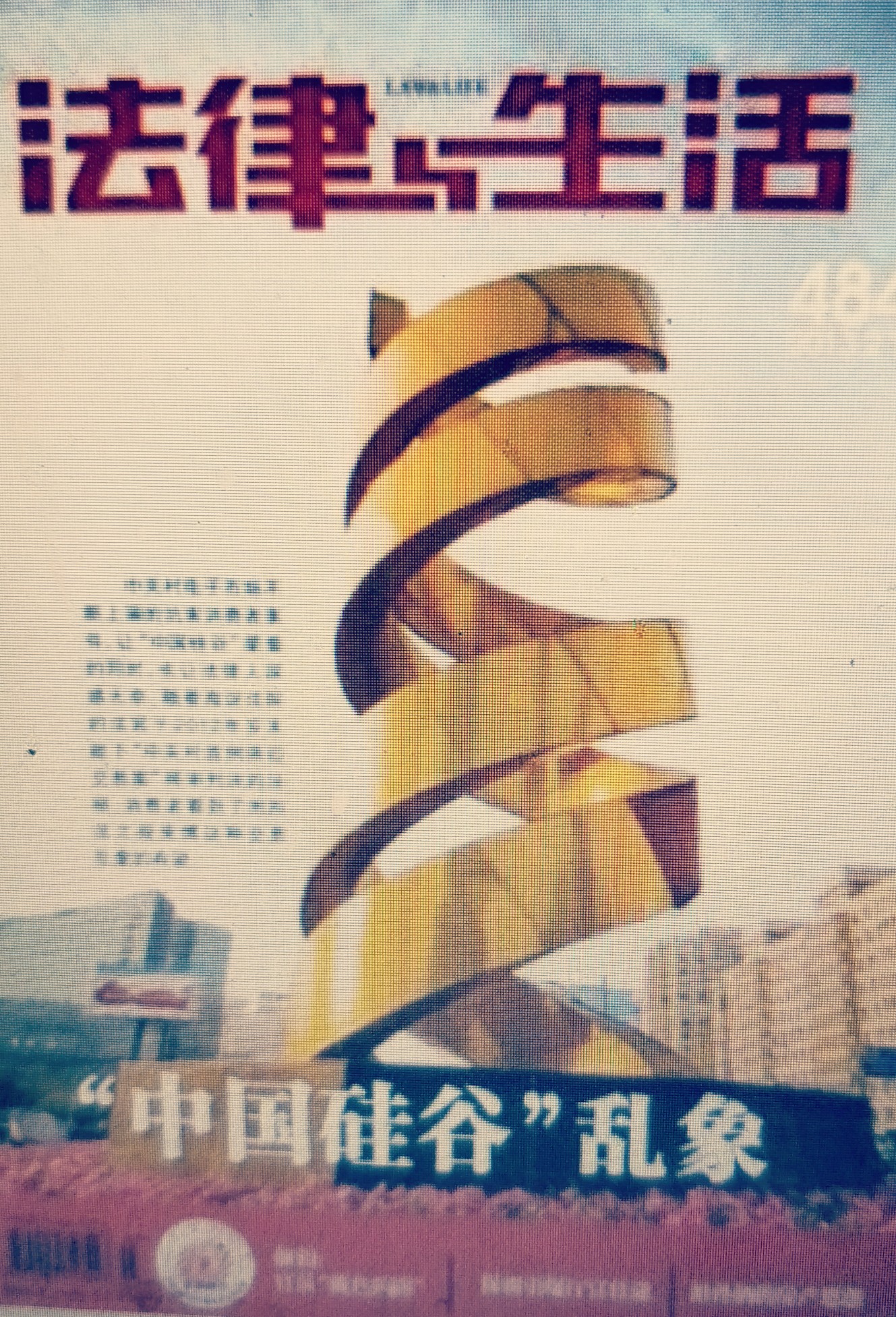 《法律与生活》杂志封面
《法律与生活》杂志封面
2008年7月《赢在互联网》一书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出版不久就得到诸多媒体和学界的关注,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学术成果,是中国第一部互联网通俗哲学,也是中国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标志性思想成就,是中国原创的新文化、新思想、新哲学突破性发展的见证,被称为“互联网轴心时期民权的哲学、快乐的哲学,是中国新千年新思想崛起的端倪。”此书从概念提出,论证创作,到最后出版,几乎整整耗费了我十年时间,对它今日的成功,作为始作俑者,也确实感慨良多。
记得作家王小波有一篇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边的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王小波是这样给这只猪画像的:
“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见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说实话,王小波的文章与书我看的很多,但给我印象最深刻,我也最爱的就是这只猪,这是一只非圈养的猪。但我后来发现,并不是谁都喜欢这只猪,因为我曾经试图给朋友讲这只猪的故事,但几次之后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回应,哪怕一笑呢。于是,我感到一丝悲哀,也更加喜欢这只猪,慢慢我发现其实我的处境也跟这只猪差不多,我们共同的特征就是“非圈养”。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有一种谬论,说目前的中国不可能出现思想或文化的大师,他们的佐证就是现在大师似乎太多了,标准就是“伟大领袖”的标准,就是拿“伟大领袖的圈”来套。小时侯听老人们讲苏联曾经用类似的圈套过中国的苹果,但我没有经历过。
后来,又换了圈,这就是“博士圈”,也就是说一个人有没有思想,要看他是不是博士或院士。
再后来,还出现过“论文圈”,也就是一篇文章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思想,首先看你的论文写的规范不规范。
于是,尽管我们的各种科学院越来越壮大,尽管我们的博士越来越多,尽管各种报刊发布的论文也越来越规范,但仿佛这个时代有思想或敢思想的人越来越少。
别的不说,就那几个圈都套过后,很多学人也就认栽了,的确中国当下没有什么思想家,也没有什么文化大师,好象我们真的生不逢时。于是,“圈”里养的标准猪也越来越多,存栏可宰指数也越来越高。
但我仍然认为自己很幸运,我时常庆幸自己不是圈养的猪,每当我看到那些博士被强奸的时候就痛苦,每当看到他们被宰杀的时候我就希望他们得到的是真的宰杀或死亡,我愿为他们早一天能真正超脱去祈祷。
我更庆幸自己是非圈养,尽管我也曾无数次希望自己被圈养,但最终还是为自己没有被圈养而感谢上帝。就像王小波的猪一样,也曾经非常乐于吃知青提供的猪食、乐意被知青称为“猪兄”,但最终还是因为学会汽车鸣笛而被追杀,最终走上了“獠牙”之路。
起哄理论是针对权威主义和权威体系提出来的,是对权威及权威体系下的非权威、非体系内话语权的肯定。《赢在互联网》一书,从对人类数千年文明史追溯到互联网社会,所提出的“起哄权”的概念,被认为意义重大,其影响将不亚于现代民主、自由的概念。
其实,起哄理论早在1998年就提出来,但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关爱,始终没有登过什么大雅之堂。到2000的时候,我发现起哄理论实际上是互联网的核心哲学,于是进行了轻微的调整,把起哄理论与互联网哲学放在一个桌面上开始研究。因为不能得到任何官方或传统媒介的支持,2002我自己花钱创建了起哄网专门传播起哄理论,也由此起哄理论开始风靡互联网,尽管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或媒介的支持和肯定。一直到2006年的时候,《中国青年报》一个叫黄少华的记者写了一篇《我是“哄客”,我在搅动网络江湖》的文章,文章里引用了我的起哄理论一些观点,那篇文章曾经轰动一时,几乎所有的网站和媒体都转载了。即使到了今天,我也没有与这位记者联系过,由此能证明我们之间的清白,也由此可以证明他是通过起哄网引用的我的观点。
后来先后又有两个记者几经周折通过MSN采访了我,一个是上海一个时尚杂志的女记者胡悦薏写了有关我的专访《从边缘人,到互联网哲学家》,一个是北京的价值中国网的女记者覃怡敏写了有关我的专访《在互联网,谁也不能做甩手掌柜》,这几个记者没有一个曾经与我打过交道,也没有任何的朋友介绍,都是他们在互联网看到我的起哄理论文章以后、通过邮件找到我。
因为,我并不是学理科的,也不是从事IT业的,所以对互联网哲学的研究就相对困难点,所以从1998年提出起哄理论,到2000年开始将起哄理论与互联网哲学联系起来,到2002年创办起哄网,都是一点一滴的从熟悉互联网到研究互联网哲学,到渐渐肯定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轴心时期,到肯定、确认起哄理论确实就是互联网轴心时期的核心哲学,这中间的10年是非常漫长的,而这10年则有另一帮人通过互联网成就了世界首富的梦想。
其实,早在2006年就开始与出版社联系出版这本书,但是一直不能得到认可,尽管这样我并没有任何气馁,因为我明白这是一个“非圈养的哲学家”必须经过的洗练和磨难。
到2007年的时候起哄理论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但出版社依然还是问题。
直到2008年与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接触,经过专家几轮的看稿,最后可能是受胡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友对话的鼓励,出版社最后还是在2008年7月推出了这本书,几经周折我也在北京奥运开幕前拿到样书。
最后想说的是,一个以互联网为轴心的时期已经到来,人类的确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文明社会,互联网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释放了人类被封建时代、工业化社会所压抑、隔离的那种原生态的起哄精神——人类精神最伟大的核爆炸能量,可以说人类文明的新篇章已经徐徐拉开。
(本文刊登于《法律与生活》2008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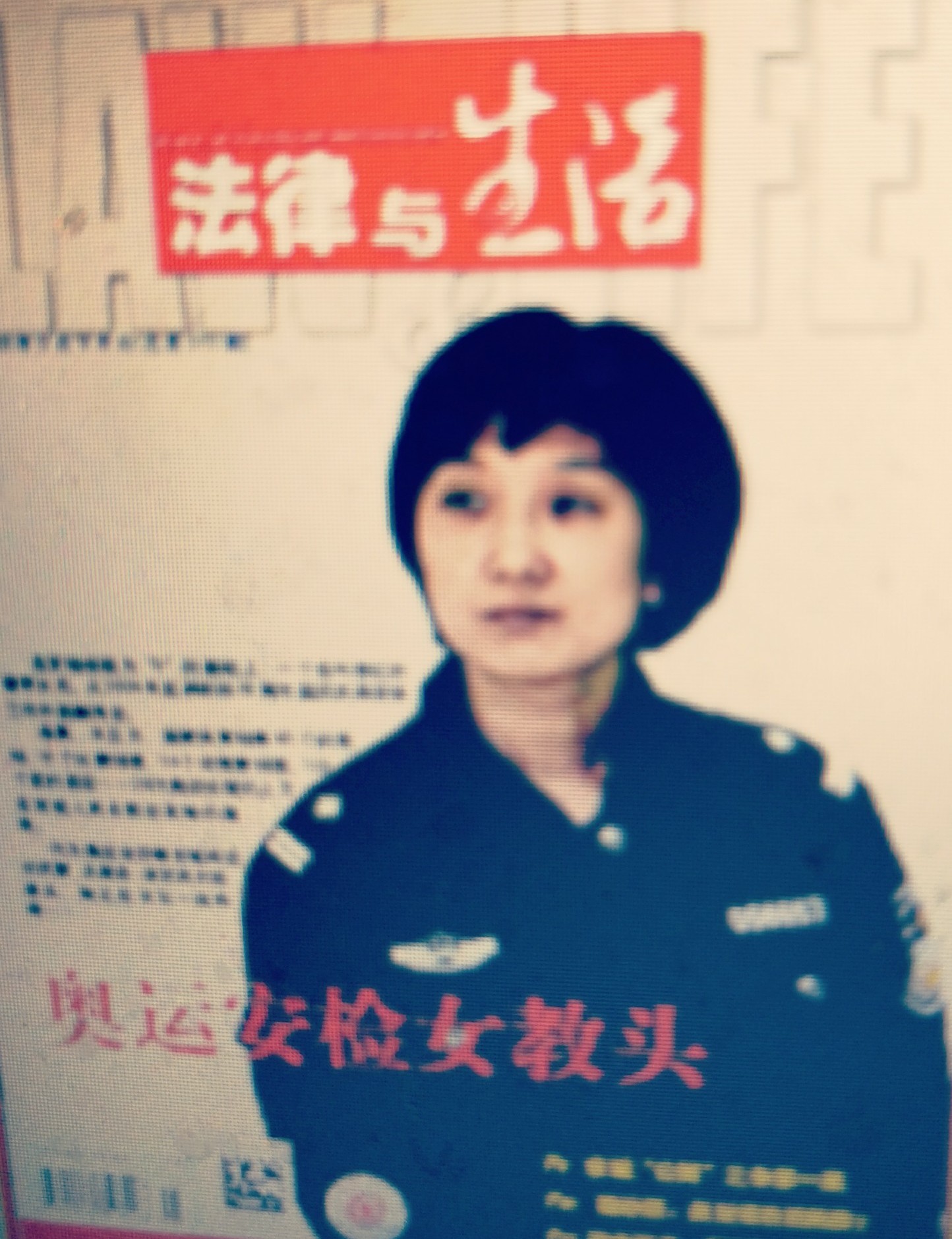 《法律与生活》杂志封面
《法律与生活》杂志封面
简介: 《法律与生活》杂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法律出版社主办,中央级法制新闻刊物,在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中国法律界名牌杂志。荣获中国期刊方阵双奖期刊奖。
